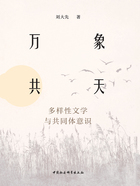
四 “新时代”的实践
以上简要的分析,萃取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理念的三重传统:一是本土经验中“因地制宜”与“大一统”辩证互存的历史传统,即由先秦元典所构筑的宇宙论中的“五方之民”“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念,“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方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愿景。它们形成了儒家意识形态主流,与强势国家一起构成了多样性统一体的延续。二是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共和”与“移风易俗”的现代性传统,近现代中国继承了前现代帝国的遗产,在向革命中国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共和”的观念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设计,吸收了共产国际理念结合本土现实,形成了“不同而和”的重叠认同和协商共识,同时又与现代化改造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后一点尤其重要,对这段历史的厘析,有助于认清作为“同时代人”的不同民族之间“不齐而齐”与“不同而和”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确立团结、和谐、共同繁荣的基本观念。三是差异与平权的多元文化主义传统。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全球性宏观政治的退潮与微观政治的背景中,来自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各类“后学”与铺展开来的文化多元主义,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汇入中国的文化实践之中。90年代之后,“资本—权力—科技”结合与消费主义,使得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普遍影响,由此也引发诸多不满。这几种传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实践中复合在一起。
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化多样性理念更多集中于多元文化主义话语,对本土历史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缺乏有效发掘,而这直接关乎文化安全与国家认同问题。在这个普遍性共识断裂的时代,观察者发现,民族国家的危机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之间的纠葛,如何认识自我与他人的认同,凸显为时代命题。史密斯(Anthony D.Smith)在讨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时候,分析了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的差别:个人认同是多维度的,家庭、性别、阶级、地域、宗教、族裔和民族都能构成其基础,这些认同之间偶尔发生摩擦,但极少真正形成冲突;但集体认同则会受到外在性、黏合性的特定束缚,对某种集体认同的忠诚有时候会受到绑架。20世纪末以来,确实出现了跨国公司、金融组织、经济活动跨越国家的现实,但主权国家依然是资源调节与分配、政治与社会行为以及国际交往中的标准单位,而为了应对全球化的交往和碰撞,洲内联盟和其他一些依靠诸如宗教联结的组织也在谋求某种超越民族主义或者超级民族主义的形式。他以欧盟为例进行了分析表明,这种设想与操作事实中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因为文化融合(合并认同)与合并主权并不相同,而通过共享记忆和经验——比如神话、传统的积淀与塑造,以及社会规划性的努力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都还在未知之数。[47]2020年2月1日,英国公投正式脱离欧盟,其原因我们无法尽言,但其结果倒正是表明了联盟共同体的岌岌可危。而一切共同体认同,显然包含了统合多样性存在的两方面内容:其一是象征、符号、记忆与价值的主动构造;其二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利害关系。当然,如果置入历史语境中来看,还包括一个面对共同危机的前提,近现代时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殖民与帝国主义入侵。
回到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认同现实中来,当下也面临着国际与国内的双重难题。一方面,中国作为“跨体系社会”与“文明综合体”国家,在国际语境中如何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文化统一体;另一方面,在自身内部则要同时协调不平衡多样性,凝聚众多不同诉求和观念为一个文化统一体。如同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说:“大多数民族国家根本没有同质的文化实体,非但如此,积极而活跃的抗争与竞技此起彼落的情况,方才是当代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显著特征。这并不是一个夕日余晖的现象,并不是少数氏族的拥护者们为了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求生存,反之……这个现象大约是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国家普遍出现的重大‘发展’趋势”[48],他在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与认同的表述中,指出其中表述上的悖论:往往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不自觉地合并,而文化主权也容易被等同于国家主权;一方面先验式地强调多元精神的必要,另一方面则又必须以现有的民族国家格局作为捍卫文化的依据。这种矛盾并不是如他想象的,靠“全球化”话语取代“帝国主义”就能解决,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扩散的过程没有实质性的高压胁迫,但是问题在于隐形的“资本—权力—科技”操控,形成了一种无法逃避与选择的结构性压迫。在后现代学者和推崇全球化的人看来,全球化有去中心的效果,似乎弱化了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好像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也不能幸免,但晚近情势的变化,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回归,多元文化主义得到再讨论,新冠疫情更使这一问题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出来[49],逼迫学者必须回到现实。目前看来,尚未有任何替代性模式与单元能够取代主权国家,而内在多民族与文化多样性的中国在这种情境中也会被倒逼出主动或被动的民族主义思潮。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怎么样将“一体”和“多元”统摄在认同之中这样经久不衰的话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并没有过时。
从经验上来说,建构认同有两条相辅相成的路径,一条是通过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在明确的意愿与规划中进行制度设计与规范基础上自上而下的推广,比如公共文化的塑造,但它往往容易走向文化的标准化与大众化,进而压抑多样性与原创性;另一条是大众的动员,文化的政治化,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拥戴,但这个过程容易形成民粹主义和排他性的极端化。中国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复合传统在此就成为有待汲取的思想资源,长久共生共荣而没有发生根本性断裂的传统构成了共享记忆和经验的积淀,成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那些民俗、神话与传统也并非天然与自发的,而是在自在的“历史流传物”基础上计划与努力的社会制造物。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准民族主义认同建构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黄河母亲、长江长城、“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文化象征与神话符号,但在20世纪后期以来,有必要激活新的“传统”,因为此前的文化话语系统,可能排除了多民族的符号,比如彝族的虎、壮族的蛙、北方民族的“熊图腾”、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不同文化……也即是说,之前摹仿式民族主义的建构法,在全球性的差异与分歧的时代失效了。“传统”在现实感的意义上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不断自我更新的流动性存在,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面对跨国资本、国际金融、互联网络、生态与性别、NBIC技术、消费主义这样的普遍性问题时,保持与现实密切关联的特殊性问题意识。那么激活有机总体性的历史感,就是必然的选择。杨念群在讨论“大一统”历史观的时候,强调应该结合与协调国家行政治理技术与边缘族群自身的历史记忆和主观意念,其实就是对“大一统”与“因地制宜”传统的现代性转换。[50]
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塑造与“世界”的重绘,即“人民共和”与“移风易俗”传统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共同利益与共同理想的结合。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而铸牢当代中国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因为发达工业社会和新兴数字社会所带来的风险(金融、战争、技术、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供应链(人、财、物、技术、市场)的整合结构而增强了。后现代的共识性断裂与个人重新原子化等问题,正源于具有共同理想与利益的未来愿景的失落。晚近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新冠肺炎及各国的应对措施中,可以看出来,在共同风险中,共同体的信任、团结与友爱是如何重要。塑造一种既继承传统,又符合现代性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迫,在中国的不同层面得到了认识和行动。它被官方话语表述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是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实际上是期望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不同途径联结起来。而从国际层面来看,“一带一路”的倡议,则在东部与西部、中国与南亚内亚、第三世界与南南合作的遗产上,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有着区别于宰制性意识形态、单边主义和资本全球化的明确指向。
今日回眸中国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复合传统,正是为了考察、梳理中华民族赓续不绝、唇齿相依的多样性文化之间共有、共享、共存、共荣的谱系,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迷思中走出[51],树立起承传流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使得不同地方、差异族群在交流融合的当代实践中纳入到中华民族新时代共同体认同之中。这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与夯实,并且使得知识生产落脚于实践、传播之中,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加深各民族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强化各民族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从而规避共同风险的可能性,在根本上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改进在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形象与文化权重。
[1] 马克·里拉认为:“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的论题从事的写作并不是在做几何学的室内游戏;他们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程俊英、蒋见元注:《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3页。
[4]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30—833页。
[5] 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1—207页。
[6] 徐乾学等编:《古文渊鉴》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8]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页。
[9] 郭璞注,邢昺疏,李传书整理,徐朝华审定:《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01页。
[10]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上,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页。
[11]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8—360页。
[12] 方勇译注:《墨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9页。
[13]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247页。
[14] 关于这一问题历史脉络的梳理,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5]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61页。
[16] 吕正惠的《杉山正明教授的中华文明观:〈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值得一读,张志强主编《重新讲述蒙元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17] 陈得芝:《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209页。
[18] 关于“新清史”各家、批评者及国内的反应,简略而直接的一本参考文集是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 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唐代文化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4—87页。朱振宏:《大唐世界与“皇帝·天可汗”之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20] 钟焓从清朝官修辞书中的君主称谓排序、“皇帝”在君权中的上升、藏传佛教法王在君主名称中的缺席以及君主的“同文之治”理想做了分析。参见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158页。
[21] 关于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的来龙去脉以及他用“文化建构论”对曾静的“本质化”的思想改造,参见[美]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生动有趣的《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温洽溢、吴家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另一个译本是《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邱辛晔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
[22] 雍正皇帝编纂,张万钧、薛予生编译:《大义觉迷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3] 雍正皇帝编纂,张万钧、薛予生编译:《大义觉迷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4] 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92页。
[25] 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26] [美]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27] 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253页。
[28] 林孝庭:《民国初年国民党民族政治之再思考(1911—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29] 杨松:《论民族》,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页。
[30] [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229页。关于“中华民族”的观念史研究,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1]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可以从政务院申请少数民族贸易、教育和卫生额外的补助经费。《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少数民族贸易、教育、尾声会议的报告的决定》(1951年11月23日通过),《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32] 《宪法草案贯彻着民族平等互助的精神》,《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33] 《怎样宣传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2页。
[34] 汪锋:《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三编,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2页。
[35] 邬国义、胡果文、李晓路撰:《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8页。
[36]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37] [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38]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0页。
[39] [英]沃特森(William Watson):《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很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问题。
[40] David Theo Goldberg,ed.,Multiculturalism:A Critical Reader,Oxford UK & 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4.Amy Gutmann,ed.,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41] Brian Barry,Culture and Equality:An Egalitarian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325.
[42] 陈燕谷:《文化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道》第三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43] [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7、329页。
[44] 刘大先:《远道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240页。
[45] [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46] [美]考恩(T.Cowen):《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王志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7] [英]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172页。
[48] [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49] Tariq Modood,Multiculturalism:A Civic Idea,Cambridge & Malden:Polity Press,2007.
[50] 杨念群:《“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165页。
[51] 刘大先:《积极的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的超越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愿景》,《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