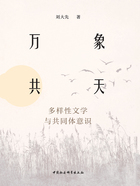
三 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与差异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处于冷战格局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路线之争中,基于革命传统又迫于内外压力,因而强化了阶级话语,但即便在最为激进的时刻,文化表述中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多样性依然得以展示,并且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主要方式之一,甚至成为彼时最为令人关注的现象。比如从1949—1979年,电影中涉及多民族题材的有《内蒙人民的胜利》(1950)、《金银滩》(1953)、《哈森与加米拉》(1955)、《猛河的黎明》(1955)、《暴风中的雄鹰》(1957)、《牧人之子》(1957)、《苗家儿女》(1958)、《五朵金花》(1959)、《金玉姬》(1959)、《友谊》(1959)、《云雾山中》(1959)、《天山歌声》(1959)、《刘三姐》(1960)、《羌笛颂》(1960)、《柯山红日》(1960)、《五彩路》(1960)、《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远方星火》(1961)、《摩雅傣》(1961)、《阿娜尔罕》(1962)、《鄂尔多斯风暴》(1962)、《农奴》(1963)、《金沙江畔》(1963)、《冰雪金达莱》(1963)、《冰山上的来客》(1963)、《阿诗玛》(1964)、《草原雄鹰》(1964)、《天山的红花》(1964)、《景颇姑娘》(1965)、《黄沙绿浪》(1965)、《沙漠的春天》(1975)、《阿夏河的秘密》(1976)、《山寨火种》(1978)……影片中除了像抗日救亡、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主流历史叙述,也关乎民间故事改编、跨境民族友谊等题材,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爱情情节在反抗压迫、侦破敌特、劳动生产中的穿插,丰富了阶级性和集体性话语主导下叙述的多样性光谱,从而也在教育、宣传、感化、斗争的主基调中增加了通俗性、娱乐感与接受度。
在美术领域如同电影领域一样,也有着超过同时代文学书写的题材扩展与形式创造。叶浅予《中华民族大团结》(1953)、董希文《春到西藏》(1954)、周昌谷《两个羊羔》(1954)、黄永玉《阿诗玛》(1954)、李焕民《初踏黄金路》(1963)、朱乃正《五月的星光下》(1963)、阿鸽《彝寨喜迎新社员》(1975)、马振声《凉山需要你们》(1976)……这些油画或国画作品中,边疆风景、民族人物、服饰建筑、习俗民情等不仅仅是某种“异域风情”的存在,更是吸收了民族民间的素材与美学观念,并做了现代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独特作品,洋溢着积极明朗、清新刚健的韵味。可以说,正是因为多样性的存在,才使得“一体化”时代的艺术作品在美学品格上再没有陷入同质化之中,反而开启了新型的文化生产道路,一直延续到当下。只是在后续的发展中,这条带有启蒙和理性色彩的新文化道路逐渐由主流退缩为支流。
20世纪60年代之后,全球性的激进革命普遍发生了宏观政治的退潮,由此带来宏大叙事的失败,解放政治、左翼革命及其背后的启蒙叙事、思辨哲学、进化论、阶级论话语逐渐失效。与此同时,其能量转移到微观政治领域,身体(性、LSD)与身份(族群、性别)问题被提升强化,后现代、后殖民、解构主义、新历史叙事学、女性主义、生态话语等陆续登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去殖民化斗争后,从政治到学术思想上的反思与推进;就后发国家与发展中地区而言,20世纪上半期反帝国主义、反殖民运动与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彼此促进,造成了整个世界格局的转变,从“不结盟国家”“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到“第三世界”理论,亚非拉的前殖民地或后发地区纷纷建立自己的国家并试图树立自己的话语。两方面构成了冲突、对话与调适,而最终伴随着市场、资本、消费主义的扩散,逐渐形成了一种价值多元的无意识。还有一个原因是,新兴科学与技术对于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影响。20世纪以来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量子物理、波粒二象性、混沌数学、控制论、信息论……改变了对于牛顿力学世界和启蒙理性的认知,一度被工具理性、数理逻辑压抑的非理性、“元逻辑”“诗性智慧”之类在新的时代被萃取、提炼,生发出各种歧异性话语。边缘群体、少数者的权力、多样性的存在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对于平等和承认的诉求,逐渐发展为多元主义的理论与行动。
价值多元与合理性的分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从政教一体中分化,形成价值观的多元。社会群体发生分化,如同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说:“它就会日益需要和倾向于超越它原先在空间、经济和精神等方面的界限,除了单一的群体开始时的向心性外,在日益增长的个体化过程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它的各种要素的摩擦中,增加一种离心的倾向,作为通往其他群体的桥梁。”[36]这个个体化过程同时也是与普遍化互动的过程,即形成新的历史主体与历史话语的过程。个体化与普遍化良性而平衡的互动才会产生有活力的文化。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早期过于强势的阶级与革命话语在激进化过程中难免会部分遮蔽多样性,从而造成整个文化生态的失衡。80年代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时代某种程度上让“现代化”形成了新的全民族的“态度一致性”,延续并改变了革命年代文化多样性的形态,到了90年代因为市场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席卷而来,尤其是伴随世纪末全球化的到来,多元文化则构成又一种传统。
近代以来进入到世界史叙述的中国文化多样性已经不能仅在中国范围内理解,而应该将其置于全球的复合语境之中,理解其文化交融与文化间性。到了改革开放的此际,中国融入全球的程度则更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20世纪70年代初期视为“后现代”开始的时间,而从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到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几乎都同意,“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话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37]。与此同时的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因为民权斗争和战后移民问题的现实,而逐步采纳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倡议,在国家内部是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权利合法化;就国际上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则将文化多样性作为先验式的命题。多元文化主义存在不同理念,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将文化多元主义分为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框架内的以及对民族架构进行回应的三个阶段,并在“西方民主国家”内划分了少数民族、移民、奉行分离主义的种族宗教群体、非公民定居者、种族等级群体五种类型,具有“政治含混性”,“有时被自由主义用来反对守旧和狭隘的民族文化观,而有时又被保守主义者用来捍卫守旧和狭隘的少数群体的文化观”[38],因而在各个国家表现不同。南非自1948年开始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至1997年永久宪法生效而结束),是为了限制白人权利,而马来西亚1974年实行九个政党的“国民阵线”,内在实质却是“马来人优先”[39]。这些含混而诉求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上囊括了一系列的边缘群体,包含诸如性别、宗教的少数派及各类亚文化等问题,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原住民的身份与认同上,以反对种族歧视、承认的政治和文化自由为基本诉求,[40]进而在教育、就业、政治选举、经济发展、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实现权利平等。
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名实相违的情形,像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所说,多元文化主义生发的问题跟它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追求,从两个方面使得广泛的平等政治更加难以成功。从最小的方面来说,它转移了政治努力的普遍目标。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严重毁坏有利于机会与资源全面平等的组成联盟的条件”[41]。一方面它可能只是资本掩盖其实质性压制的话术,从而引发了诸多批评[42];另一方面,在后现代语境中,因为对于历史进化论的摒弃,多元文化主义很容易滑向缺乏共通价值标准的相对主义,使得平等尊严政治向“差异政治”转化。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仔细分析过平等尊严政治与差异政治之间的差别,前者确认的原则普遍地意指同样的东西,而后者要求我们给予承认的是某个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是它们与所有其他人相区别的独特性。这有其“本真性”和内在性的现代合理性,但是“它有权要求我们以假设其具有价值的态度来研究不同的文化,但却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最终做出的判断承认它们具有很高的价值,或者具有与其他文化平等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不同标准的视界融合……这里涉及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强行要求肯定的价值判断,这种行为是同质性的,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也许我们还应当说是悲剧性的”[43]。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执法造成黑人死亡事件,所引发的BLM(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贵”运动)抗议,这当然是奴隶制度、种族主义和阶级分化的恶果,在疫情焦虑和党派斗争之下,蔓延为全国性带有民粹性质的运动,却也暴露出多元文化主义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多元文化主义原本不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所要面对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现实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也已经从理念上解决了平等和承认的问题,但多元文化主义在翻译的旅行中强化了文化性与差异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到中国语境之后,成了文化话语中前提性的存在,而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早期的“积极的多样性”理念。后者正如前文所说是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视为一种过程与实践,而指向于未来某种理想主义的构想;但在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某种具有普遍影响的思维定式之后,文化的差异性往往不自觉地被做了本质化的理解,从而使得文化多样性本身成为目标。也就是说,当我们论述到文化多样性时,它成了叙述与思考的框架,而不再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某个问题或主题——文化因此被凝滞化和静态化了。在实践上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带有“地方全球化”性质的文化(创意)产业。举例而言,从《印象·刘三姐》开创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化印象生产”与“文化符号经济”的旅游观光模式,“通过将某些标志性元素从其原生处抽离出来,通过夸张的手法将其精细化与精致化,达到直击式的一眼难忘的传播效果。因而,‘印象’的生产必然会走向刻板印象的生产”,“对于金钱和物质的欲望,显然是现代商品化、市场化的一种共通,但某一特定文化群落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需要为自己建立一种特殊性或者差异性……差异性非常重要,因为具有差异特征的文化符号可以成为象征资本,这种资本能带来其他的利益……‘文化差异性’或者‘多样性’,其实可能根底里恰恰表明了我们时代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同一性”[44]。到21世纪之后,差异性更加变成了不证自明的正确与确凿无疑的真理性论述,这个时候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超越了内容或者“问题”的层面,而成为思维或者“方法”。
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形解释为历史主体性弥散的结果,乌托邦耗尽能量之后溶解了的现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离散出来的个体、地方与族群小型共同体、民族国家……被叙述为彼此冲突而对立的存在,共同利益至少在某个层面上被打破,而共同理想则退隐为口号式的存在。于是,多样性变成了差异性,带来了“政治正确”的褊狭与相对主义:(1)差异的绝对化,比如世俗化背景中的宗教基要主义;(2)差异的符号化,对文化商业性与景观化的开发、销售与消费;(3)差异的虚无主义,颓废与“丧”的逃避与虚幻的快感追求。而这一切背后“不在场的主人”则是“资本—权力—科技”三位一体的统治:从生命政治到精神政治的结合体。
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化不可能最终意味着地方性的终结,而是发生了转型,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空间之中”[45]。同质化、差异化、杂交化成为当下时代文化的风貌,这不是用经济学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46]就可以解释的,“世界主义”也不过掩盖了“资本—权力—科技”统治的真相。多元文化主义原本作为一种民主与平权举措,有其现实意义。如果将这种手段当作目的,就走向了其反面,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诸多反思。但作为一种在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话语,已经进入中国当下文化之中,因而也是我们需要在厘析中扬弃式继承的传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