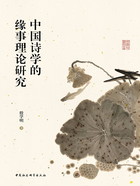
第一节 哲、事、诗
诗与“事”和“哲”到底有何关系?古人虽未明言,却有迹可循。首先,诗与哲理既自相抵牾,又密不可分。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2]。准确地说,诗既有“文”的别趣,也有“理”的极致,只不过“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3]。其次,事与哲理相为表里,穷理而见事。宋代上蔡学派的创立者谢良佐指出:“天下多少事,如何见得是处?曰:‘穷理便见得。事不胜穷,理则一也。'”[4]最后,诗与事相推相生,故有“ 《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事”既是诗的动力因,也是构成因。诗与诗学的高度在“理”中发见,审美在“文”中显现,品性则在“事”中形成。为此,我们将在儒、道、释的哲思中发掘“事”以及“事”与诗和诗学的诗性关系。
一 儒如是所言事、诗以及诗学
何谓儒?儒,从人需声。本义为柔,术士之称。儒与事有何关系?儒者又是如何看待和言说事的呢?儒家经典《礼记正义》解释说:“指其所营谓之事”,“事谓人之所营事务也”,“夫事是造为,造为由民,故先事后乃有物也”。[5]从此意义上看,“事”就是人与物(人)相互营造的一种行为结果。事非己所欲,何以为之?熔儒、道、墨为一炉的《淮南子》指出:“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6]由此看来,人之所以操劳于事,与人生存之需休戚相关。对儒家而言,操劳不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是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在儒家看来,“事”有“小人之事”和“大人之事”,即劳力与劳心之分。儒家更倾向于后者,即立德、立言和立功的劳心之事。基于此,《释名》云:“事,伟也。伟,立也,凡所立之功也。”[7]儒家勤事立功,不仅看到了事的客观性,而且也看到了事的运动性。宋代大儒程颢、程颐《论事篇》云:“一事息则一事生,生息之际,无一毫之间,硕果不食,即为复矣。”[8]如其所言,人就是在一件事接一件事的事件流中生存的,别无他径。儒家从人之所需的历事生存中感悟和理解事,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缘事诗学观念。
(一)立身之道:鄙事多能,敬敏于事
从生存的角度看,“事”究竟对人有何作用?儒家的基本观点是,躬行鄙事、敬敏于事,足以立身成人。在儒家看来,躬行鄙事是人多才多艺的前提,敬敏于事是人现世生存的法则。换句话说,诗性的人生缘于世事的磨砺。对此,《论语》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9]
从太宰与子贡的对话以及孔子的自述来看,人的多才多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历事尤其是在凡鄙之事中磨砺而成的。朱熹就指出:“言由少贱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尔,非以圣而无不通也。”[10]何以见得?人在历事的过程中不是消极应对,而是不断反思、调整和创造自我的。换句话说,人不仅在事中认识自己,而且也在事中创造自己。故俗语有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章学诚也指出:“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11]从此意义上说,“事”构成了人的本质属性,具有生存论的意义。儒家的道德、伦理、诗学等知识体系一般是在历事生存的实际需要中建立的。或者说,儒学的知识多从“事物”和“心事”中获取。正基于此,子思“格物”之“物”并不单是客观之“物”,而更多训为“事”,尤其是洒扫、应对、进退之“事”。阳明“良知”也并不单于心上求之,而更多是在“事上磨砺”得之。正由于儒家善于“托事于物”,在诗学上既形成了物感说,也形成了事感说。在诗史上,既有汉代“缘事而发”的乐府诗,也有杜甫“即事名篇”的诗史、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讽喻诗。可以说,儒家事论奠定了诗与事的紧密关系。
如果说儒家“躬行鄙事”是人自下而上的生存之道,那么“敬敏于事”则是现世生存的原则。第一,“敬事而信”的生存法则。儒学创始人孔子对人有两个要求:一是“作己以敬”,二是“修己以安人”。安人在修己,修己在作己,作己在恭敬。子曰:“居处恭,执事敬。”(《论语·子路第十三》)即“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12]。在儒家看来,敬与信是立身、处事之本。第二,“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处事原则。孔子认为对事不仅要敬,而且要敏。朱熹认为,“敏于事”之事是“所行之事”,“当为即为,不失其几也”。[13]在儒家看来,由于“事”是瞬息流动的,即“生息之际,无一毫之间”,只有敏于事才能把握住时机而成事,即孔子所说的“敏则有功”(《论语·阳货第十七》)。很显然,《尔雅》所云“事,勤也”,与儒家事论思想是一致的。在儒家看来,如果言不顺了,事就不会成。因此,人不仅要“敏于事”,还要“慎于言”。当然孔子在强调敬敏于事的同时,也强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事),即“无多事,多事多患”的思想。
一言以蔽之,“敬”是儒家行事的态度,“敏”是儒家处事的方法,“信”是儒家做事的原则,而“鄙事多能”则是儒家的生存理念。从诗学的角度看,正因为有了“敬”的观念,《诗三百》才立经成典;正因为有了“敏”的思想,儒家诗学才盈千累万;正因为有了“信”的操守,儒家“以事系诗”的诗评模式才得以形成;也正因为有了“事事躬行”的务实精神,儒家诗学才成为中国古代最接地气的实用诗学。
(二)文质彬彬:从礼处事,体仁为事
简而言之,儒家处事之道有二:一是“敬以直内”的仁,二是“义以方外”的礼。前者为质,后者为文。文质合一,名正事顺。《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14]
第一,礼者,即事之治,儒家从礼处事。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15]也正是基于此,荀子才有“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以礼处事”可以说是儒家最重要、最有效的处事原则和方法。据《左传》记载: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认为,“先封”理应优先为长。滕侯则认为,周之卜正,不可以后之。最终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礼消除和平息了争端。先秦列国明卿、行人在朝礼、观礼、宴礼以及盟誓、缔约等外交场合常常伴随着各种诗学活动,比如言《诗》、赋《诗》、歌《诗》必以礼相偕。《仪礼注疏》有“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之说。《毛诗》亦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论。总而言之,不管从朝觐、聘问还是赋诗、言志,儒家一般是以事见礼的方式处事的。
第二,仁者,事之体,儒家体仁为事。《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从二。”[16]樊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17]朱熹进一步指出:“体事,谓事事是仁做出来。”[18]在朱熹看来,“仁在事。若不于事上看,如何见仁”[19],“事”又是如何显现“仁”的呢?其中“贞”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周易》曰:“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20]朱熹解释说:“‘贞者,事之干’,彻头彻尾不可欠阙。人之遇事所以颓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贞故也,此所谓贞,固足以干事。”[21]在孔子看来,君子体仁为事,故“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见利行事,故“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论语·子路第十三》)。在儒家看来,做事不能不仁不义,因为事的本体是仁义。扩而言之,儒家是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之法才得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的。
儒家的礼与仁互为表里,二而为一,故有“克己复礼为仁”之说。从诗学的角度看,“《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是仁的延伸,而“发乎情,止乎礼义”则是礼的训诫。正由于仁的诉求,儒家更倾向于伦理的诗学。正由于礼的讲求,儒家更侧重于规范的诗学。又由于礼与仁都缘于事,从而使儒家诗学不仅于外有礼的形式要求,而且于内有仁的内容要求。儒诗及其诗学中的历史内容、美学诉求多与事、仁、礼有关。
(三)温柔敦厚:中事之诗,有为之学
儒家敬敏于事,进取有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实为中庸之道。其为人、为诗,温柔敦厚、无思无邪。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22]其实所谓“敦厚”就意味着“思无邪”,即孔子所云:“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3]所谓“温柔”就意味着主文谲谏,必不狂狷。在孔子看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即“过犹不及” “不得中行而与之”。[24]通俗地说,“中行”就是行事不偏不倚,乃得其中。在孔子“中行”思想基础之上,荀子还进一步提出了“中事”的概念。荀子有云:“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25]与之相反,“事行失中谓之奸事”[26]。在儒家看来,事行于中,则得其正。对诗而言,就是要作中事之诗。所谓“中事之诗”就是诗之事要中,诗之情要正。比如窈窕淑女,君子何求?既不能狂,亦不能狷,而是于人不淫,于己不伤。此即孔子所云“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先儒谓《关雎》之诗,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至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谓乐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贤才,至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所谓哀而不伤也。”[27]后来,杨载在《诗法家数》中也指出:“征行之诗……要发兴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时感事,触物寓情方可。”[28]由此看来,情要正、事要中是儒家对诗的基本要求。也正是基于情正、事中的诗学原则,儒家才创造出大量温柔敦厚的诗篇。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汉代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取决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有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之学就是有为之学。由于儒家奉行“敏事慎行”的处事方法,儒生才皓首穷经,诗论才浩如烟海;由于儒家践行“敬事而信”的处事原则,中国诗学才不失其真、薪火相传;由于儒家“缘事而发”的感发思想,诸如“即事名篇”的现实主义诗歌才熠熠生辉;但同时也由于儒家有“成事不说,遂事不谏”的保守观念,使得其著述多“述而不作”“以经立义”,从而使得儒家诗学也有陈陈相因、生搬硬套、缺乏创新的瑕疵。但整体而言,由于儒家有为之学是以中事原则建立起来的,其诗温柔敦厚,其学不偏不倚,故功多大于过。
二 道如是所说事、诗以及诗学
道为何物?庄子曰:“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29]儒家和道家都言道,不过在道家看来,儒道是“有为而累者”的人道。当然正是在“有为”的人道观念下,儒家才敬敏于事、鄙事而多能。然而道家却认为,“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于是道家更看重“无为而尊者”的天道,对事的态度自然与儒家有所不同。相对敬敏于事的儒家,《汉书艺文志》如是界定:“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30]道与事有何关系?“秉要执本”的道家又是如何看待和言说事的呢?
《淮南子》云:“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31]何以如是说?《说文解字》云:“道,所行道也。”[32]其注云:“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33]道者,人之所行也。行者,事之所成也。事行有道,不可离也。儒家与道家都言道和事,但二者却有很大的区别。儒家的道多是人道、立身之道,对事既敬又敏,追求有为有功;道家的道多是天道、率性之道,对事既避又匿,强调无为无名。儒家与道家对事的观念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儒家从“事”对人的建构意义上理解“事”,而道家则从“事”对人的异化意义上理解“事”。在道家看来,“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34]。正基于此,道家对物、人、事的看法才与儒家有所不同。庄子指出:“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35]
道家一方面承认事的客观存在性即“不可不为者”,但另一方面,又在主观上尽量回避事以达清虚自守。在道家看来,“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36]。可以说,道家开拓了一条与儒家不一样的处事道路。道家对事的态度直接影响对诗与诗学的认识,自然飘逸、冲淡清虚的诗风以及意境、文外之旨的诗学思想与道家的处事理念有着很大关系。下面笔者将通过对道家处事观念与方法的研究,揭示出事与诗、诗学之间的发生关系和运作规律。
(一)自然之道:弃事形不劳,无事而生定
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注重对人以及人性困惑的思考。老子曾感叹:“人之迷,其日固久。”[37]继而他指出:“清静恬和,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养不悖,知事之制则其举措不乱。”[38]在人性方面,儒、道两家都承认,不可学而在人者谓之性。不同的是:儒家强调“性相近,习相远”,即后天“化性而起伪”的教化功能,反映在事上就是敬敏于事、修辞立诚;道家与之相反,反对一切“可学而能、可事而成”的起伪行为,反映在事上就是清虚自守、无事而生定。在道家看来,性定由于无事,无事由于心静,心静由于自然。自然之道才是万事万物的大道。
在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看来,道由于“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9]可以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是道家处事的最高原则。为何自然之道是人道的最高法则呢?在道家看来,一方面,是由自然之道的首要地位决定的。老子认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40]另一方面,也与人道自身的缺陷密切相关。老子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41]也正由于此,道家才极力维护天道的自然性,而批判人道的异化性。《庄子》云:“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42]在道家看来,儒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对人的自然性的损害,因为“事”不仅劳人之形,而且伤人之神。也正基于此,庄子才提出“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的思想。与之相反,人心中有事,就会神生不定。庄子解释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43]另外,“事”的矛盾性也扰乱人的心性。《庄子》有言:“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44]对此,庄子的主张有二:一是“无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45];二是“弃事”,“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46]。在道家看来,弃事无累,无累性定,性定自然。这与儒家克勤毋怠、化性起伪的入世观念显然不同。
由上观之,儒、道两家都承认“事”存在的客观性,不同的是:儒家积极入世把“历事”视为人性完善的途径,而道家清虚自守把“劳事”视为心性紊乱的根源。道家“无事而生定”的思想对诗以及诗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在对诗人“如婴儿之未孩”本心的守护、对作品透彻自然的崇尚以及对诗歌境界的开拓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除烦省事:为不为,事无事
道家认识到“事”对人心性扰乱的一面而强调“无事而生定”,甚至提出“弃事”的主张。从此意义上说,道家是被动的、消极的。但也要看到:道家在“弃事”的背后也有积极的、主动的处事哲学。其中“为不为,事无事”与“除烦省事”的思想与方法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为无为,事无事”是道家处事哲学的最高境界。在大道不行、天下大乱的年代,道家是很矛盾的。一方面,道家看到事对人身心伤害的一面而主张“弃事”;另一方面,道家也看到事是“匿而不可不为者”,即事是客观存在的而只能“接于事而不辞”。但与儒家深入其中敬敏于事不同,道家则置身其外“为无为,事无事”。这种置身其外并不是彻底的消极遁世,而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诗性“敞开”和迂回的“主动”,这恰恰成就了道家的高度和深度。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47]因此,他极力主张“为无为,事无事”[48]。老子所谓“为无为,事无事”其实并不是事事不为、事事不做,而是任其自然、无为无所不为。老子曰:“逍遥乎无事之业。机械智巧,不载于心,审于无假,不与物迁,见事之化,而守其宗。”[49]《关尹子》有云:“道本至无,以事归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运事者,周之百为。”[50]从诗学影响来看,道家“为不为,事无事”的思想对中国诗人胸襟的洞开以及诗歌境界的拓展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想必李白“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的佳句只有在“事无事”的胸襟洞开下才能创作出来。诗之旷达、褊狭的格调与经事的胸襟有很大关系。白乐天的诗句“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被誉为“达者之词”,孟东野的诗句“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被贬为“褊狭者之词”,与二人在事上历练所形成的格局直接相关。
第二,“除烦省事”是道家处事的原则方法。西汉河上公对老子“事无事”的解释是“除烦省事”。道家在现世生存中为何要除烦省事?这与事由简入繁的本质特性有关。庄子就认识到:“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51]王充指出:“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52]正是由于“事”由简到繁甚至千反万畔,道家在处事时才提出了“除烦省事”的原则和方法。
“事”之所以难知,与事本身有关,同时也与人自身有关。在道家看来,“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53]。《淮南子》指出:“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54]面对事“剪不断,理还乱”的本质特性以及人的心术公患,道家的处理方法就是“除烦省事”。在老子看来,“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55]。《文子》引老子云:“不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56]与之相应,《周易》亦有“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思想。在道家看来,与其浑水摸鱼、身心俱疲,不如闲庭信步、愿者上钩。从诗学角度看,道家“除烦省事”的处事方法以及对“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的认识对中国诗学尚简风格的形成以及“诗无达诂”诗学命题的理解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飘逸自然:无事之诗,无为之学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曾指出:“老子之学,避世无为之学也。”[57]儒家诗学是有为之学,自然在诗歌创作上提倡经世致用,即所谓“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也。与之相反,道家诗学是无为之学,自然在诗歌创作上提倡飘逸自然,即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也。相对而言,儒家诗学强调诗之用,道家诗学注重诗之体。清代诗论家薛雪《一瓢诗话》曰:“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58]从儒、道两家诗学的区别来看,儒家多为敦厚之人,诗必庄重、有事有情;道家多为倜傥之人,诗必飘逸、无事无情。如何理解道家的无事之诗,其审美价值究竟何在?道家的无为之学对无事之诗以及言事诗有何影响?下面笔者将剖玄析微、由表入里一一辨析。
何谓“无事之诗”?道家的“无事之诗”真的是无事、无情吗?笔者认为,所谓无事之诗主要是指道家在清虚无事的状态下所创作出的恬静深远、飘逸自然的诗歌。其中玄远之诗是道家无事之诗的典型代表。宋代著名词人、史学家宋祁把“老子《道德篇》”视为“玄言之祖”。及至“汉之仙术,元与黄老分途。魏晋之世,玄言日盛,经术多歧。道家自诡于儒,神仙遂溷于道”。“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59]魏晋之世,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道家无事之诗尤其是玄言诗可谓盛极一时。由此看来,道家做事无事事之心,作诗则无事事之诗。这种诗并不是与事毫不相干,而是用无事的心隐匿诗中之事,从而形成飘逸自然、游心物外的审美风格。道家无事之诗除了冲淡朴拙、清新脱俗、宁静玄远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无事之心应无为之事。嵇康“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故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佳句。宋代全真道第六代掌教宗师尹志平亦有诗云:“收拾轮竿罢钓钩,诸缘顿息便休休。情忘意灭无多事,彼岸高登不用舟。”再比如,郭璞《幽思篇》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可谓无事,然而这种冲淡朴拙的景物勾画只是景物勾画?而不是“假外物之象以喻人事”?汤用彤在《言意之辨》中指出:“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60]
中国古代诗歌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写物、情和理时一般将“事”隐含起来,其实在诗歌的内部,“物”是“事物”、“情”是“事情”、“理”是“事理”。无事之诗并不是没有事的诗歌,而是事蕴其中的诗歌。道家无事之诗需要“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中国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长篇叙事诗,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与道家无事之诗的传统以及感观事物的方式有很大关系。道家见素抱朴如婴儿之未孩,其无为之学涤除玄鉴、坐忘心斋而清虚自守、无为而无所不为。中国古代诗歌之所以飘逸自然与道家清虚自守的无为情怀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境界多是道家提升或开拓的。
老子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61]如果说儒家诗学的“常有”是一种修辞立诚的有为之学,从而实现了诗歌的实用性存在,那么道家诗学的“常无”则是一种飘逸自然的无为之学,从而实现了诗歌的本体性存在。前者是实有的缘事,后者则是虚有的缘事。道家鼻祖老聃为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与儒家相比,道家虽出于史官,但对事却有了超越现实的新认识。在中国古代,儒道缘事的互补使得诗歌既有言之有文的“徼”,又有文外之旨的“妙”。
三 释如是所闻事、诗以及诗学
明代文学家袁中道在《柞林纪谭》中有段关于道与释的经典论说:“问‘叟于释迦、仲尼、老子三人何居?’曰:‘释迦不论智愚贤否,只要他了生死。老子则有无为之学问矣。释迦不可及矣,吾庶几者其老子乎!'”[62]释迦不论愚贤而只了生死,有执空超越的信念。如果说儒家是有为之学,道家是无为之学,那么释家则是色空之学。王维的诗之所以有空灵之感,不能说与佛没有直接的关系。其诗“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道出了其中缘由。
(一)破迷开悟:因缘而起,先除事障
在释家看来,人生之所以苦,主要是由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缘造成的。“无明”和“行”是人的前世,“识”到“有”是人的现世,而“生”和“老死”则是人的来世。人要打破因缘的苦海轮回就要先除事障。如何破除事障呢?《圆觉经》指出:“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63]如何破迷开悟呢?在知身心皆为挂碍后,就需要净心而远离于心事。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在释家看来,因有“四事、九事、二十九事”。比如“九事”是指众生事、受用事、彼因起事、起已住事、彼灭事、彼种种事、说事、所说事、徒众事。如何处理这些事呢?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摄事分齐” “远离心事”。《如楞伽经》就有“远离于心事,不得说惟心”之说。南朝佛教史家僧祐亦云:“夫事起必由于心,报应必由于事,是故自报以观事,而事可变。举事以责心,而心可反。”[64]
六朝以后,佛教对中国古诗的影响毋庸多论。单就缘起观念和对事的超然态度来说,其影响就不可小觑。且不说王维,就是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杜甫也常游佛寺,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譬如上元二年(675)杜甫蜀州之作《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知君苦思缘诗瘦,大向交游万事慵”就很有如是见净心的佛性。此所谓觉知诸缘事,无量思量常不断。就诗学而言,缘事诗学观念或多或少也受到了释家缘起论的影响。严羽的《沧浪诗话》更是以禅喻诗,不必多使事,从而开创了妙悟之说。
(二)色即是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从佛法上看,“永舍贪欲,先除事障”是见性成佛的修身之方。但从佛理来看,心无挂碍如明镜,世无有恐怖、无有事烦。之所以心有烦事只是由于凡夫无明以及贪、嗔、痴等欲望造作而成的。释家的这种理念可用唐代宰相陆象先的名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加以概括。当然佛氏之空与老子之无是有所不同的。《朱子语类·释氏》解释说:“佛氏之空,与老子之无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无了’。”[65]通俗地说,释家比道家“无”得更彻底,四大皆空了。《心经》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66]明代文学家高濂指出:“ 《心经》曰:‘色即是空’,非无色之空,恐人执色为碍耳。‘空即是色’,非有色之色,恐人执空为碍耳。色空双泯,心境一如无纤尘可拂,方是了然旷达。”[67]苏轼有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
世人对释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认识虽褒贬不一,但其对艺术境界的开拓性尝试还是有审美价值的。清代画家华琳指出:“禅家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真道出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也。特恐初学未易造此境界……在空白之处,令人一眼先觑著。”[68]试想王维如果没有“空不异色”的佛家理念的话,那么就很难创作出“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样空灵的诗句来。可以说,释家“色即是空”的理念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的创作有着重要的贡献。在一个世事纷扰的尘世之中,怀揣“天下本无事”的诗性情怀去创作诗歌、构建诗学,这样诗歌会具空灵性,这样诗学也更具超越性。
(三)空灵圆觉:息事之诗,执空之学
释家的诗有空灵圆觉之感。究其实质,与其先除事障、息事宁人的佛理有关。释家强调四大皆空,会稽元真子董德宁称其为“执空之学”。可以说,“空”使释与儒和道明显地区别开来。从诗与事的关系看,如果说儒家之诗是温柔敦厚的“中事”诗、道家之诗是飘逸自然的“无事”诗,那么释家之诗就是空灵圆觉的“息事”诗。在释家看来,凡夫的苦海源于种种无明的事障,脱离苦海而见性成佛,就要除事障、息人事。《息诤因缘经》就有“能令诤事而得息灭”的说法。道家无事与释家息事不同,前者基于此岸,追求无事性定;后者出于彼岸,追求息事怀空。
首先,在观物取象上,释家执空之学阻断了诗人世事的袭扰而能直观事物的本质,从而使得诗更具通透性、超越性。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南北朝佛教涅槃学的代表人物谢灵运的山水诗中的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从而使人就是人,诗就是诗。释家执空之学与儒家有为之学、道家无为之学不同,释家以息事怀空的理念来观物取象确实铸就了不一样的诗歌形态。
其次,在命意遣词上,释家执空之学滋养了诗人闲云野鹤的情性,从而使诗的内容与形式更具空灵性、脱俗性。释家诗内容空灵、形式脱俗,究竟如何实现的呢?魏庆之《诗人玉屑》引《西清诗话》杜甫言:“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69]释家于诗有超凡脱俗的,也有精雕细刻的。贾岛推敲成诗精于雕琢,严羽以禅喻诗力避浅俗,提出了“学诗先除五俗”之说。
最后,在参诗品诗上,释家执空之学使诗人四大皆空,从而使诗更具妙悟性、滋味性。释家的禅宗派主张参禅见佛,这种思想对中国的诗歌影响非常大。宋代诗论家包恢解释说:“大概以为诗家者流,以汪洋淡泊为高,其体有似造化之未发者,有似造化之已发者,而皆归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以前辈尝有学诗浑似学参禅之语。彼参禅固有顿悟,亦须有渐修始得。”[70]诗只有熟参才能“谓之顿门” “参诗精子”。严羽也曾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71]中国古代诗歌在欣赏品评时往往不做推理判断,而是在非理性的顿悟之后体味不可述之事的妙趣。
四 小结
一般而言,某种诗学理论的高度往往取决于支撑它的哲学思想的高度。在中国,儒、道、释不仅是中国哲学的高度,而且也是中国诗学的高度。儒、道、释对事与诗的深度言说对中国诗学的缘事理论构成、特性以及运作的方式等都有着直接的根性关系。研究儒、道、释对事与诗的言说既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事以及诗与事的关系,也有助于理解缘事诗学理论的本质及其特征。
在不同的历事过程中,儒、道、释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这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对中国古代诗歌以及缘事诗学理论的构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儒家处事求中,是有为之学,继而形成了以杜甫为代表的极具人文性和实用性的诗歌体式;道家事无事,是无为之学,从而形成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极具自然性和审美性的诗歌样式;释家除事障、息人事,是执空之学,继而形成了以王维为代表的极具空灵性和超越性的诗歌形式。从诗学的角度来看,儒家重事,从而使得中国诗学出现论诗及事的传统,“四家诗”、《本事诗》以及诗话相继而生。道家和释家隐事,从而使中国诗学形成了心领神会的另一传统,而中国诗学的妙悟品评也多与此密切相关。儒家重事,但述而不作,道家和释家隐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又共同铸就了中国诗学较少推理、不成体系的品格。如果说儒家入世而重事使得中国诗学成为实用的诗学,那么道家和释家出世而隐事则使得中国诗学成为审美的诗学。然而不管是显还是隐,“缘事而发”都是中国古代诗歌以及诗学的生命源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儒、道、释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融合的。宋代道教学者曾慥在《类说·佛书杂说》中就提出了“儒者之阳阴,老氏之有无,释家之色空,言其致则一”的思想。儒者用实,而其妙处本虚。释、道用虚,而其空处本实。中国古代诗歌以及诗学是儒、道、释相融而生,本书分而治之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诗歌以及诗学的缘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