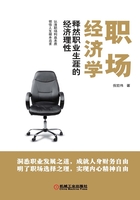
二、社会文化问题及其管理原因透析
如何解决理念先进与行为落后的组织文化问题,如何消除当下员工价值迷茫的社会文化问题,其实质是社会主流文化的宏观管理以及社会价值重塑的问题。而社会主流文化的宏观管理以及社会价值重塑的问题,是通过有效的国民文化道德教育去实现的。因此,我国社会文化问题,既与我国社会价值变迁轨迹密切相关,又与我国国民文化道德教育状况紧密相连。
(一)国民道德教育与社会价值变迁回眸
文化的核心内核是价值观,我国社会文化当下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价值观的宏观引导与协同管理的问题。廖小平(2013)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轨迹大致如下:
第一,改革开放前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取向。新中国成立后的“单位社会”和“单位体制”,与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以及由短缺经济所导致的共同贫穷是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的,这就构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公私对立和政治挂帅、斗争哲学和继续革命、高度集权和一元化领导等方面。改革开放前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取向深深根植于当时的社会土壤和时代特性之中,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取向,是改革开放前最突出、最鲜明、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迁。1978年以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单位—个人”的“单位社会”转型为“国家—社会(包括社区、职业团体、中介组织)—个人”的“后单位社会”,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的所有制“主体多元结构”。在此社会背景下,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总体镜像是: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在这场社会价值观变迁过程中,过去的社会核心价值发生了解构,包括:“革命与斗争”“重义与轻利”“集权与人治”“身份与等级”“崇高与信仰”。与此同时,社会价值观变迁又建构了以下核心价值,包括:“市场与契约”“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治”“道德与诚信”“富强与文明”“发展与和谐”。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解构与建构的演变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反思与博弈,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的深刻嬗变,21世纪以来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重构(廖小平)。
(二)我国社会当下文化问题的主要表现
概括地讲,我国社会当下存在于一些人之间的文化问题主要表现为:物质金钱崇拜,实用理性与感官主义交织,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从政治崇拜转为娱乐崇拜,崇尚谋略家。
1. 物质金钱崇拜
由于一些国人对物质金钱的崇拜,利益令他们变得越来越冷漠。物质金钱崇拜实际上并不能使人感到幸福和尊严。对于这些人来说,“发财”成了唯一的“硬道理”,拼命地去占有、掠夺、囤积、挥霍、炫耀。崇尚物质金钱崇拜的人没有精神信仰,甚至笃信精神信仰可以通过金钱购买。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金钱至上,除此之外均不感兴趣,便形成了《人民日报》有篇文章所说的“无智无趣是中国当下文化最主要的特征”的后果。
2. 实用理性与感官主义交织
顾远2001年就曾指出:经济增长给长期受到精神和消费压抑的人们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传统的实用理性便成了“以满足感官享受为人生内容,以‘跟着感觉走’为人生哲学”的感官文化。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等成了一些人的中心话题和追逐对象。如果任其发展,实用理性的传统智慧可能被感官主义所扭曲,阻碍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
3. 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
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特点就是“祛魅”,用调侃、娱乐的方式来解构一切“形而上”的东西。比如,曾经非常流行的“赵本山现象”,每年春节联欢晚会大家就等着看他的小品,看完以后就打牌去了,这就是快餐文化,大家哈哈一笑,笑完了以后心中什么都没留下。
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使人们没有“敬畏心”。有学者认为,有了敬畏之心,人才不会忘乎所以、无法无天。敬畏之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另一个后果就是使人们患上“浮躁病”,做事时更倾向于选择投机取巧。
4. 从政治崇拜转为娱乐崇拜
纵观美国《时代周刊》涉及中国人物的封面秀,似乎能够描绘出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不同历史时代的中国人崇拜偶像的图谱与脉络:从早期的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到如今的周星驰、章子怡、韩寒、李宇春。即是说:中国社会的崇拜是线性的和单一的,也就是用一种崇拜去替换另一种崇拜,偶像的地位逐渐被市场经济下多元、绚烂、娱乐大众的歌星影星所取代。21世纪全新的电视娱乐文化与网络文化之中诞生了复制美国娱乐节目“美国偶像”的“超级女声”——这一由电视、网络、手机共同打造的全民选秀运动。在新的时代下,更专注地投入到造星运动全程的追星族们的新称号是“粉丝”,亦显示了西方文化正比西方商品更直接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5. 崇尚谋略家
我国具有“崇尚谋略家”的文化传统。刘亚洲上将指出,“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地纪念,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史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1]
6. 国民文化道德现状的当下问题描述
北大教授陈浩武指出,我国目前“在文化层面也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缺乏道德的一种倾向”。“美国论坛对中国人的负面评价”一文对我国当下国民文化道德的问题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
我国国民文化道德现状的当下问题简要描述为:①一些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②一些人老想走捷径,倾向于索取而不是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③一些人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可。“面子”是他们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他们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④一些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降临。但声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
(三)社会价值与国民道德重构问题透析
面对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了社会价值的重建:①2001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提出要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②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③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④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概括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从国家层面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从社会层面讲,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奉行的核心价值理念;从公民层面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公民道德行为的本质属性。
1. 我国小学、中学、大学国民文化道德教育的问题
许多资料与现象显示,我国的大、中、小学校的国民文化道德教育管理工作,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年代并不成为其管理重点,其国民文化道德管理效果也不容乐观。
第一,升学率和就业率对我国各类学校国民文化道德教育的冲击。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中小学校以学生的升学率为主要指标,大学以学生的就业率为主要指标;中小学生以学习知识和应对考试为重点;大学生以学习知识和求职择业为核心。而国民文化道德教育仅体现在小学的德育课、中学的政治课和大学的一两门基础课上,对于这些课程,形式上老师教了、学生学了,但问题是学习这些课程的重要性和投入远远低于升学率与就业率,其国民文化道德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学校教育组织的文化道德理念的价值起点过高。我们仅以中、英、美的小学生守则作比较,就足以看出我们的组织文化从小学开始就有“完人”的价值取向,起点过高,相对缺乏“人本”价值吸引力与“人本”价值亲和力[2]。
第三,学校国民文化道德教育的内容设置和可接受性问题。我们的组织文化从小学开始就有“完人”的价值取向,其教育效果不容乐观。然而,社会道德大厦有层级结构之分,道德提升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上台阶,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2. 我国企事业组织的国民文化道德教育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事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国民文化道德教育主要通过组织与企业文化的形式进行。由于组织(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重组织外部文化建构、轻组织内部文化建构的倾向,最终导致员工对组织价值理念缺乏信任,形成了“文化理念天上飘,员工行为地上爬”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