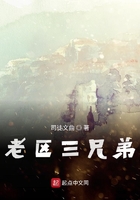
第9章 以粮換瓮再卖粮
添雄外出时,随身携带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是在歇息时听的。那时,寨背还没有通电,他与外界的联系就靠这个小东西了。
他从广播里听到,中央一年给农民下一个一号文件,说的都是农村的事;他还听到,每逢夏收和秋收时,国家都公布粮食最低收购价;那价格一次比一次高,早稻价格已经从一角伍分,长到了三角钱,两年长了一倍。
他在走村串户时发现,家家都有余粮了,但是,农民兜里还是瘪瘪的,见到稀罕物就拿粮食換。有许多农村妇女相中了他驮的瓮,想用稻谷折成现金去跟他换。
添雄想赌一把,按现行价格收粮換瓮,瓮能挣一把,再等收购价格涨了,粮食还能挣一把。
要干这个买卖,一个人不行,得有人帮忙,他想到了三个人。
一个是添培,他们厂里有拖拉机,他在县城还能联系县米粉加工厂,帮他卖粮;
另一个是添忠,他今年15岁了,就要初中毕业了,考高中没有把握,上县里读书,家里也供不起。他聪明,稳当,会记帐,还会木工,跟他出去可以亦工亦商;
再一个就是添培的弟弟添洪,他比添忠大一岁,和添忠是同学,就同自己和添培一样,形影不离,他木工也出手了,和添忠可以搭成一副架。
他算了一笔帐,雇拖拉机一次能拉60口瓮,一口5元钱是300元,而拖拉机送货,一天也就200元。以粮換瓮,以运费和代销费为由,每口瓮加价5元,农户能接受,等于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能弄成这一步,那就有帐算了。一口大瓮能换150斤秈稻,60口能换9000斤秈稻,按这两年的长价趋势,一斤涨7分钱还是有把握的,那么一趟就能赚630元。收一季粮往往是一个月,做10趟就是6300元。
想好了就做,这是添雄的一贯作法。瓮的订单订好了,就雇拖拉机。
添培厂里的拖拉机都是送来维修的,维修好了要试车,添培买通了试车员,挑周六出去,周日晚上回来,都不要运费,几包香烟,两顿馆子就搞定了。
添雄不打无把握之仗,事先把添忠、添洪派去收粮,兼做木工,拖拉机一到就卸瓮装粮,一点不耽搁时间。
最大的风险在运瓮上,添雄和添喜砍了不少竹杆子,劈成竹扁担型,装车时把瓮口都用竹子夹上,用绳子逐个捆紧,再用蒿草塞满空隙。
作坊的工匠们给他出了招,叫做重物难移,临开车时,他们把每口瓮都加了水,把瓮口用塑料布扎上,每个瓮从50斤增到了200斤。
这招还真好使,60个瓮拉出了20多公里,无一损毁。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粮食拉回后,在加工厂附近以每月100元的价格,租了一个房子,用茓子围了粮囤。
三间房能排开直径两米,高两米的囤子12个,每个能囤6立方,稻谷的体积大,六立方折合5吨粮。
制瓮作坊的老板见添雄一次能销出这么多瓮,把积压的300多口瓮都赊给了他,还让工匠加班加点,以7天出一窑,一窑100口的速度为他制作。
屋子装满了,添雄停手了,一个月,走了12个点,收上60吨秈稻,拉出了760口瓮,损失了40口,共负债1.2万元。
接下来,添雄几乎钻进半导体里了,焦急地听着消息。
一过五一劳动节,电波里传来了喜讯:1984年夏粮收购价格——早稻每公斤0.76元。
添雄雀跃了,每斤涨了8分,他的粮食能卖到45000元了。
但是,他高兴早了,加工厂收粮是要验等、验水、去杂的。
验等全凭检验员的嘴,他说几等就几等,几乎没有一等的,添雄的粮被验了二等,每斤0.35元;
验水还可以,有验水仪器,添雄收的是陈粮,水份低于18个,不扣斤,超过18的,每超一个点,100斤要扣一斤的;
去杂又是检验员说的算,张嘴就是3个杂,即100斤扣3斤,谁跟其理论他就加一个杂,再理论再加,添雄爱钻牛角尖,结果被扣了5个杂,6000斤粮食不翼而飞了;
过完秤,12万斤秈稻成了11.6万斤,再去掉6000斤,剩11万斤了,一结算是38500元;
最不能让添雄忍受的是只给他兑现了19250元现金,打了19250元欠条,要到年底才能兑现;
添雄看到其他人都是这样,也不再钻牛角尖了,但是他也心寒了,不想,也不敢再做粮食生意了。
好在到年底,欠债能还上不说,还能剩5000多元,再捉摸别的干吧!
添忠和添洪第一次外出,一个月里长了不少见识,两个人不回家了,干上这个活就找下个活,干脆不报考了,也不上学了。
添忠和添洪,一个沉默寡语,一个爱说爱笑;一个做工细致,一个快手快脚;一个尊重兄长,一个友爱弟弟;两个人性格互补,相处融洽,堪称绝配搭挡。
添洪家庭条件好,阿爸有退休工资,哥哥又在城里上班,姐姐又多,生活无忧无虑。
添忠却不然,阿爸留给他的是债务,虽然有大哥顶着,但是他也想为家里尽一份微薄之力,起码不想靠家里养活。
他想继续读书,但不想让大哥太操劳了,上高中要去县里住宿,动辄用钱,他多希望有一种勤工俭学的学校,让他圆了读高中、上大学的梦。然而,现实很残酷,他只有认命了。
添喜和阿妈在家种地,看到妈妈整日地劳作,还得给他洗衣烧饭,心疼妈妈,便拼命多干活。
虽然三季稻改成两季了,但是那些农活仍然没有闲歇。
从立春开始,就要收拾油菜,耙田整地,买种吸苗;
惊蛰车水灌田,春分插秧;
清明收割冬麦,谷雨翻地种红薯;
立夏间种苞谷,小满收割早稻;
芒种耙田吸苗,夏至又种二季稻;
两暑烈日炎炎,又该给晚稻锄草、喷药、追肥;
立秋和处暑,离开水田上梯田,担水浇红薯和苞谷,也要锄草趟地扶垅;
白露黄烟上架,开镰收晚稻,秋分整田种萝卜;
白露收红薯,寒露收苞谷,立冬种冬麦;
小雪大雪刨冬笋,冬至收完萝卜种油菜;
小寒大寒不清闲,忙着祭祖过大年。
这就是寨背农民的一年,男人出外打工、经商算是轻闲自在的了。女人在家,正所谓大活随节气,小活连天干,日初就下地,日落就入眠,360天,天天不得闲。
寨背的女人,不!客家人的妇女都是大脚,并且一年四季打赤脚,那是劳动生活使然。
1984年的最后一天,添雄算回了欠款,还清了所有债务,全家人都吐了一口气,欢欢喜喜地准备过大年,1985年的春天,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