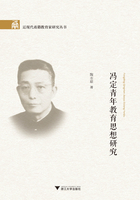
第二节 宣教志业成就“不可多得的教育人才”之美誉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冯定先后在新四军、抗大第五分校、淮北区党委、华东局从事宣传工作。
一、在新四军从事的宣传工作
冯定在新四军先后担任过宣传科科长、《抗敌报》的主编、干部教育科科长、江南澄武锡区军政委员会副书记、澄武锡区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副校长、中共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拂晓报》的主编。所有这些工作都与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分不开。
1938年10月下旬,冯定由组织委派,从上海经过温州、金华,进入新四军的军部驻地——皖南泾县云岭。1938年10月26日,冯定在《译报周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脑子还得磨砺》。1938年11月,新四军正式成立宣传教育部,朱镜我同志任宣传教育部部长,冯定任宣传科科长。由袁国平同志任书记,加上朱镜我和冯定共三人,成立了党报委员会,决定由冯定兼任《抗敌报》的主编。冯定后来改任教育科科长,最后改任干部教育科科长。
冯定除了在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主编《抗敌报》外,还常去教导队讲课。当时新四军除了一个直属团、教导队、服务团驻在云岭一带以外,还有三个支队,一支队的司令员是陈毅,二支队的司令员是张鼎丞,三支队的司令员是谭震林。作为支队司令员,陈毅和其他支队司令一样,有时也来政治部和宣传部,与冯定等人谈谈军事情势、部队情况等。这样冯定和陈毅的接触就多起来了。在皖南军部时,有的同志被怀疑成“托派分子”而准备让他们离开新四军,冯定就亲自去找项英,为这些同志申诉,请求把他们留下来,最后项英同意了冯定的意见,把这些同志留了下来。
1939年春夏之际,经过上海共产党组织的筹划,为了扩大新四军在上海的影响,组织几位进步的新闻记者来云岭访问。他们临回上海时,相约要求宣传部同志们用新闻体裁写些东西,设法寄到上海发表。其后不久,适逢三支队在繁昌红杨树连续几天和日寇对抗,打了胜仗,冯定就用曾在上海用过的笔名写了一篇通讯,其中还用“据说是共产党员”的口气提及一位战斗英雄的名字。寄至上海后,文章先在日报上发表了,当天又在晚报上发表了,看到的人都很兴奋。此外,冯定仍用新闻记者的口吻写了《项英将军访问记》,寄到上海后在一个叫《学习》的进步刊物上发表了;此后又写了《陈毅将军访问记》,1939年4月20日和27日分为上、下两篇以“贝叶”的笔名在上海《译报周刊》第2卷第1期和第2期上发表,向上海及沦陷区各界民众宣传新四军高级将领及新四军的抗战主张,扩大了党的抗日武装新四军的影响。当冯定把对陈毅的访问记呈给陈毅阅读并请教时,陈毅微笑着说:“对我的赞扬有些夸张了。”不过他接着说:“只要新四军的旗号和我们的名字能在进步的上海报刊上披露,终是对抗战有好处的。”
1939年岁末,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从政治部干部中抽调了六七个人,建立了一个巡视团,到陈毅部队即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开展巡视工作,进行部队的调查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冯定是巡视团的成员之一。巡视团的工作,除了初到时列席江南特委扩大会议听陈毅同志和其他领导发言以外,就是在支队司令部的领导下做些整训工作。经过整训的有老二团、江抗二团、四团和司令部直属的教导队等。1940年春节过后,由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大约3月初,军部来电要袁国平只身急速回去处理事情。袁国平临行匆促,没有来得及向冯定当面交代,便托人传话给冯定,告诉他巡视团暂时不回去,留在一支队司令部,要冯定暂时负责一下巡视团的工作,什么时候回军部听候军部电示通知。这一决定让冯定躲过了人生一劫,袁国平回军部后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这样一来,冯定实际上已是直接归陈毅领导了。后来,回军部去的交通断绝,巡视团的整训工作也难以再开展起来。陈毅在一次高干会议上决定开辟江南地区,冯定要求参加开辟工作到前方去。陈毅开始时说:“你们是军部派来的干部,我不好分配工作,要等军部命令。”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冯定就随陈毅同志的一支队到苏北去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皖南军部了。后经组织允许,大约在1940年5月,冯定随王必成的老二团进入江南丹阳一带,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二位首长的领导下工作,冯定担任江南澄武锡区军政委员会副书记。项英打电报给陈毅,对冯定做出的评价是:“该同志是不可多得的教育人才,军事非其所长。”事实上,项英对冯定的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做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和教学工作,这些都是冯定的长项,带兵打仗非他所长。其实陈毅对冯定已经比较了解,心中当然明白冯定所长之处。后来,陈毅把司令部由江南移到江北,成立了江北指挥部,并在解放黄桥镇后,任命冯定为澄武锡区政治委员,其间还成立过一个规模不大的短训班让冯定负责。1940年10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泰兴县(今泰兴市)营溪组建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根据军部的意见让冯定到江北负责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工作并任副校长,陈毅兼任校长。
话分两头,冯定暂时代理的巡视团的工作由于没有军部的指示无法进一步开展了,但冯定一直以宣传鼓动工作见长,他的宣传鼓动武器一是现场讲课,一是写文章发表在进步刊物上。1940年年初,国共关系紧张,冯定也没有放松自己为共产党用文字做宣传鼓动的工作。在1940年2月期间,冯定写过一篇名叫《美国与世界大战》的长篇论文,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的范本。冯定运用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丰富的统计资料和辩证的分析方法,把美国这个处在世界反法西斯营垒却又执行反革命两面政策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这个使多少人为之迷惑又有多少人对之畏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百足之虫,刻画得淋漓尽致。1940年2月15日和3月1日,冯定的《美国与世界大战》长文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在《抗敌报》第1卷第7期和8期上发表。1940年3月16日冯定又在《抗敌报》第1卷第9期上发表了《忠奸辩》一文,认为只要是直接或间接做着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的事,就是忠;只要是直接或间接做着危害人民、危害民族、不利于抗战的事,就是奸。
二、王元化眼中的新四军宣传科长冯定
王元化 是在20世纪30年代与冯定结识的,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冯定以“贝叶”为笔名撰写的文章。他对冯定的人品和作风,深表敬仰。
是在20世纪30年代与冯定结识的,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冯定以“贝叶”为笔名撰写的文章。他对冯定的人品和作风,深表敬仰。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抗日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掠,这些暴行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慨。日军占领北平、天津时,王元化只有17岁,那时便随家人一起流亡到上海。1938年年初,王元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由孙冶方任书记、顾准和曹荻秋任副书记的文委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1938年年底,地下党文委派殷扬(后改名为杨帆)和王元化,率领20余名文艺青年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所组织的联合慰问团前往第三战区进行慰问。党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把20多位文艺青年及其携带的抗日报刊和医药用品等,送往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慰问团行至浙江金华时,受到国民党的干扰,殷扬便嘱托王元化带一名同志先行。临行前,殷扬临时写了一封介绍信由王元化带往新四军交给“贝叶”,并让其转交给党组织。
王元化随新四军的交通员阿陀,由金华出发,途经岩寺、太平,到达泾县,当他们找到新四军军部的接待处,要将介绍信面交“贝叶”时,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一时却不知“贝叶”是何人,几经周折,才弄清楚原来“贝叶”就是冯定。冯定当时在新四军宣教部任科长。王元化被领到宣教部见到了冯定,那是王元化和冯定的第一次见面。冯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王元化。王元化那时还不到二十岁,觉得冯定比他大许多,思想水平也要高得多,所以初次见面免不了有些忐忑不安。但是,冯定与他交谈时,满脸笑容,态度平和,并不把他当作一个青年而是当作老朋友一样,一下子就让王元化感觉到冯定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
王元化在新四军宣教部暂待期间,每天都和冯定在一起。王元化在和冯定相聚的那些日子里,发觉冯定总是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兴奋地和他谈论种种问题。当时和冯定的谈话中让王元化印象最为深刻的话题是关于大城市许多知识青年涌往解放区的问题。王元化非常清楚地记得,冯定谈到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后,往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未到解放区前是满怀热情,带有一些主观幻想,以为解放区一切都新,一切都好,一点缺点也不存在;但是到了解放区之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往往不如自己主观幻想那样美好,因此未免失望,甚至灰心丧气,以至一蹶不振。冯定说,从第二阶段跨越到下一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那就是主要要看这些知识青年如何磨炼自己,克服自己的主观幻想,使理想和现实趋向一致,达到完善的融合,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革命的战士。王元化深深地感觉到冯定完全是以一个理论家的口气讲这些话的,他滔滔不绝地阐发着自己的观点,这让他与当时新四军其他老干部显得非常不一样。即使是在解放区,冯定的思想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也还是和他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一模一样,他已经习惯于把具体的事物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谈论。这一点给王元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担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从事管理与教学工作
随着盐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根据地建设和军队迫切需要大量有理想、有知识的干部,大后方很多进步青年又陆续来到盐城,他们投奔革命,参加抗日,也需要加强教育和学习。1940年11月,刘少奇和陈毅等人决定,将新四军苏北抗日军政学校和八路军五纵队教导队合并,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是在海陆中学的大操场上举行的,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的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刘少奇在谈到办抗大五分校的目的时说:“为了实践而学习理论,为了打胜仗、提高工作水平而进学校,为了养成一批军队工作干部才办抗大的。”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话,使学员们明确了学习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
其实,抗大五分校的前身是新四军一支队创办的抗日军政学校,这个学校是在1940年上半年期间,陈毅到苏北后指派冯定负责筹建的。当时,冯定两次去上海,通过上海的地下党动员和组织了一批进步知识青年来校学习。黄桥决战前,抗日军政学校在泰兴县的营溪正式开学了。1940年10月初,东进新四军一支队和南下八路军五纵队在盐城会师。1940年11月,刘少奇和陈毅找冯定谈话,刘少奇对冯定说:“我们党的事业在苏北又有一个大的发展,需要培养很多干部,现在办抗大,马上还要办党校,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1940年11月,新四军以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为基础在苏北盐城创办了抗大五分校,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陈毅兼任抗大五分校的校长,赖传珠、洪学智任副校长,冯定任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后来由余立金任主任),谢云晖任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12月1日,陈毅签署招生启事,对招生目的、条件、人数、考试科目等做了详细说明。
抗大五分校共举办了两期,学员的来源多样化,一部分是部队连、营级干部,少部分为团级干部;大部分学员是本地或上海、杭州等地来的进步知识青年。抗大五分校共有学员3004人,毕业学员有2519人,分成6个大队,其中2个女生队,每个大队是1个营的建制,大队还分政治队、军事队,学习各有侧重。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的队。陈毅在百忙中特地来分校做过形势报告。刘少奇还做了三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对学员们的教育影响很大。当时,学校还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各党小组,在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
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抗大五分校培养出不少干部,向人民军队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人才,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建设。抗大五分校设在盐城,推动了盐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盐城有许多青年参加了抗大五分校的学习,毕业后成为盐城地方干部的有生力量。抗大五分校亦曾派出人员,深入盐城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和民运工作等。抗大五分校办学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给盐城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41年7月,日伪对盐阜地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后,抗大五分校随主力转移。
抗大五分校刚建立时由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领导,1941年1月以后,由新四军军部领导。1941年4月28日,洪学智率抗大总校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的教职员工100余人,由河北邢台到达苏北盐城,增强了教学力量。冯定任第一副校长,洪学智任副校长。
由于冯定对马列主义理论有较深的造诣,所以他不只是军校的副校长,还是理论教员,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冯定讲课深入浅出,善于从具体事情讲起,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的讲课方式,对于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学员们来说,都很容易接受,而且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得很快。
四、担任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
1942年11月,冯定开始担任中共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主编《拂晓报》。《拂晓报》是1938年9月底在彭雪枫战斗的地区——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创刊的。《拂晓报》与拂晓剧团、骑兵师成为彭雪枫的三件宝。1942年元旦,《拂晓报》和中共淮北区党委机关报《人民报》合并,成为中共淮北区党委的机关报,冯定在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兼任《拂晓报》报社的社长,他离任后由邓岗同志接任。《拂晓报》现在为安徽宿州市委的机关报。
1942年3月16日,冯定撰写了《学习的中心堡垒》一文发表于《拂晓报》上,学习的中心堡垒就是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对政策、计划如果只凭主观的了解,是异常危险的,这种毛病一时不易察觉,但一旦发觉便可能已铸成大错。做好调查研究需要支部工作的教育与督促。怎样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呢?一是增强对调查研究的认识。调查研究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是作风问题、党性问题、思想方法问题,要有调研精神,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二是加强对调查研究的教育。对干部进行调查研究的教育是迫切而又需经常进行的任务。要让他们对调查研究的技术与方法熟悉,抓住各种各样的例子,分门别类、就地取材、由近及远、由小到大进行教育。三是完善对调查研究的实施。不应寄托于少数人或某个专门机关,而应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对该部门的情况与工作进行调研。
1942年7月1日,冯定在《拂晓报》上发表了《论反省》一文。冯定认为人们的反省工作做得还不够深入和普遍。他认为反省有三条重要作用:一是整顿他人莫如先整顿好自己,整顿自己莫如反省。整风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检讨思想和行动,使大家更能站稳立场、确定观点、领会方法。对每个干部来说,自己才是决定性的,己风不正,拿歪风去整人,不可能“治病救人”。二是整风对自己来说,就是要改造自己。反省不是改造自己而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改造自己的先决条件。通过反省认识自己,不但可以体会出观察问题的正确思想方法,还能对自己的历史发展有更为明确、更为系统的认识,由此“对症下药”,进行改造自己的工作。三是改造自己要理论联系实际。怎么联系呢?当然需要经常的思考和练习,而要使思考和练习更有效果,就得找典型来作为思考和练习的对象。其实关于自己的材料是现成的,所以最好的典型就是自己。
冯定还指出了反省中的几种不正确现象:第一种是极少数仇恨、厌恶整风的人,他们有的是将自己放在整风圈外,认为整风只是对其个人过不去,或者自高自大地认为本人向来是“两袖清风”,无须再整了。第二种是知道了整风的利害,但立场不正确,表现在反省上就不是真正为认识自己,以改造自己,而是为了表功讨好、文过饰非、卸责诿人、敷衍门面、试探口气、伏笔张本、放泼泄气。冯定认为:“这些都是个人主义的立场,是以个人利害作为出发点来进行反省的,所以开始总扭扭捏捏不肯反省,或者是发出反省只要自己明白自己改正就可以了的论调,或者是等待观望,看别人反省些什么再说,就是实行反省了也绝不会老老实实和坦坦白白,这对自己也不会有多大帮助。这种人首先要把立场改变过来才好。”第三种是存心整风,决意反省,可自觉文化不高,或理论不多或经验不丰,所以不敢反省、不能反省。
1945年6月23日,冯定在《拂晓报》上发表了《教育改革中应防止“矫枉过正”与“因噎废食”》一文,同年10月7日和10月8日撰写了《认清形势 积极行动》一文,分为上、下篇发表于《拂晓报》上。冯定的所作所为正印证了冯定“是不可多得的教育人才”的评语。他用手中的笔把结合现实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发表出来,呼唤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投入到正确的社会行动中,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五、为俄文翻译家的“诞生”指点迷津
李俍民(1919—1991年),中共党员,原名李恺,又名李星,镇海大碶横河小李家(今属宁波北仑区)人,是我国著名的俄文翻译家。1937年读中学时,李俍民随兄长李侠民参加“横河乡抗日救亡工作团”,表演抗日戏剧、歌曲。高中毕业后,李俍民先后担任小学校长、教务主任等职。1942年5月,李俍民去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李俍民在冯定去世几年后写过一篇《回忆冯定同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回想自己40年来在文学翻译方面能够有所成就,跟当初冯定对他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的翻译事业与冯定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原来,在1942年5月,李俍民和后来成为冯定夫人的袁方,一起随当时新四军四师联络部的徐今强,从津浦路明光小站进入苏皖边老解放区参加抗日战争。正是来到新四军四师,李俍民才得以有机会向冯定求教。据李俍民的回忆,在他们到新四军四师后不久,冯定就被调到新四军四师师部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李俍民按照大多数初进解放区的同志的做法,把名字改为李星,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第二队(政治队)学习。李俍民因为深受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同志1939年翻译的该书)的影响,立志自学俄语,准备将来像梅益同志那样,为我国读者翻译、介绍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
可是,在当时的老解放区,烽烟四起,生活非常紧张,根据地没有什么可以见到的俄文资料。幸运的是,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的宣传科科长陈遗同志送给李俍民一本上海出版的《俄华小辞典》,虽然这本小辞典总共只有几千字,但还是让李俍民如获至宝。无论政治、文化学习及军事操练多么紧张,李俍民每天总要抽出一定时间来背诵十个生字,可是这种背诵辞典的学习实在太单调枯燥、太艰苦了。于是李俍民千方百计寻找俄文报刊。但在敌后方哪里会有什么俄文资料啊!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他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天,新婚不久的袁方(冯定的妻子)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李俍民,冯定精通俄文,而且他们的新房里就有一大沓俄文刊物,由于袁方不懂俄文,也不清楚那些刊物是什么样的刊物。不过袁方说她已经跟冯定谈起过李俍民学习俄语的艰苦处境,冯定表示愿意与李俍民谈谈学俄语的事情。李俍民真是欣喜万分,自己不但有希望获得冯定在学习俄文上的指点,而且说不定还会获得一些俄文资料呢。在这种情况下,李俍民与冯定第一次见面了,他们是在冯定的“新房”见面的。李俍民看冯定的所谓“新房”,不过是向农民老乡借用的泥坯叠成的小房间而已,房内设施非常简陋,大致就是一片木板床、一张小桌子和几个凳子。但让房间生辉也让李俍民眼睛发亮的是,靠墙放的板架上放着不少书刊,墙脚边还放着一捆捆书籍,李俍民心里一阵欣喜,袁方所说的那一大沓俄文刊物肯定就在其中了,想不到自己渴望一睹“芳容”的资料就在眼前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正当李俍民心潮澎湃之际,冯定亲切地招呼李俍民坐下,这时李俍民才注意到冯定穿了套棉军服,脸色微微有些泛黄,但瘦削的脸反倒让又大又黑的两眼显得炯炯有神。冯定又是给李俍民倒茶又是给他吃糖,让李俍民倍感冯定的热情。在当时无论是茶还是糖,在敌后环境中都已是很少能见到的“奢侈品”了,因为冯定刚刚喜结良缘才弄到这么点“奢侈品”。随后,冯定询问了李俍民学习俄文的情况:“我听袁方说,你在俄文资料和辅导老师缺乏的情况下,依然在利用各种机会自学俄文,你的刻苦精神真让人佩服啊!我稍稍懂点俄语,可是我的工作很紧张又太繁忙,抽不出时间来对你进行辅导,真有些遗憾啊。不过我这里倒有一些俄文资料。”说到这里,冯定起身从他那一大堆报刊中翻捡出三本俄文刊物,并对李俍民说:“这是上海出版的三本俄文版《时代周刊》。靠你那本小辞典,可能查不到大部分生字,但是比啃辞典要好,在目前条件下,这大概也是苏皖边区仅有的几本俄文读物了。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的文学翻译工作做出贡献来。”接下来,冯定又跟李俍民谈起他当年学习俄文的情况:“我1925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文学编辑时,自学了俄语,边学边用,翻译一些小品。通过翻译来做到学用结合,真是学一门语言的好办法。”冯定从与李俍民的交谈中了解到李俍民是因为深受梅益同志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影响而发誓自学俄文的,因此告诉李俍民:“听说梅益同志也有可能要到解放区来 ,不过梅益同志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像是从英文转译的……”李俍民当时真想跟冯定一直谈下去,但考虑到冯定是首长,工作非常繁忙,休息时间又很少,不忍心继续打扰下去,就赶快起身告辞。当袁方把那三本俄文版的《时代周刊》塞到李俍民手里时,李俍民真是高兴得心都飞起来了。这时袁方才想起来告诉李俍民,冯定还是他的宁波老乡呢。李俍民拜见冯定时没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反倒是体会到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革命事业的万丈热情”。
,不过梅益同志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像是从英文转译的……”李俍民当时真想跟冯定一直谈下去,但考虑到冯定是首长,工作非常繁忙,休息时间又很少,不忍心继续打扰下去,就赶快起身告辞。当袁方把那三本俄文版的《时代周刊》塞到李俍民手里时,李俍民真是高兴得心都飞起来了。这时袁方才想起来告诉李俍民,冯定还是他的宁波老乡呢。李俍民拜见冯定时没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反倒是体会到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革命事业的万丈热情”。
1945年年底,李俍民因病回到上海,凭着那本《俄华小辞典》与冯定赠送的三本俄文版的《时代周刊》所奠定的俄文基础,李俍民进入了俄国东正教堂办的华俄夜校学习俄文,经过一段时间的俄语语法的学习,李俍民在1946年考入沪江大学外文系,两年后辍学。李俍民阅读了《铁流》《毁灭》《恰巴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部俄文长篇小说,完全掌握了俄文,终于跨入了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行列,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
李俍民一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翻译的长篇小说有《牛虻》《斯巴达克思》《孔雀石箱》《学校》《柯楚别依》《游击老英雄》《白奴》《伊格纳托夫兄弟游击队》《鹿童泪》等,翻译的中短篇小说有《一朵小红花》《游击队的儿子》《绿蚱蜢》《下雪了》《生命之爱》《斯巴达克》《两个不听话的小姑娘》《新来的》《近卫军战士马特洛索夫》《黑宝宝》《总工程师》《白桦树下的茅屋》《红海军和小黑熊》《尼尔斯奇游记》等,翻译的短篇小说有《聪明的小鸭子》《性格和真实》等。
让李俍民非常遗憾的是,1981年冯定因病在上海的华东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他却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与冯定再次交流的机会。那时,李俍民认为去医院探访冯定的人已经够多了,像他这样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也去凑热闹,定会妨碍冯定休息,于是心想还是等他康复后待自己有机会去北京时,再去拜访冯定和袁方夫妇俩。谁知不久之后便传来噩耗,李俍民竟再也没有机会跟可亲可敬的冯定见面交谈了。
如果真是人生事业途中的贵人,不在于相见次数的多寡,不在于谆谆教诲的多寡,而在于求知若渴之际给予的哪怕是一小口甘泉。对于李俍民而言,冯定在他俄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启程之际,给予了他一口值得久久回味的甘泉。
六、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1945年12月,山东分局和北上的华中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山东临沂成立,负责领导华东各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原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张云逸、舒同为常委,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工作。1947年3月,冯定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副部长,这时的华东局还在山东。1947年秋,冯定因患严重的胃病赴大连医治,手术后疗养期间,冯定撰写了多篇普及哲学知识的短文,在《大连日报》上连载,文章的总标题是“平凡的真理”,以平凡的真理之一、之二的形式进行连载。1948年,光华书店将连载于《大连日报》的这些短文辑成《平凡的真理》一书正式出版。该书是冯定的主要代表作,被誉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传最广、进步青年最为喜爱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
1949年,中共中央华东局迁往了上海,第一书记是饶漱石,冯定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副部长。这时的华东局负责领导中共上海市委、山东分局、南京市委、浙江省委等地方党组织和各项工作。1952年,冯定除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外,还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51年年底开展的针对干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年初变成了针对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后来的结果表明,初期揭发出来的那些“五毒”行为许多被夸大其词了),斗争矛头从干部转向了资产阶级。由于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在输往志愿军的军需物品中发现有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这很快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大家纷纷起来声讨,“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正是在这样激烈反对资产阶级的高潮时期,《学习》杂志发表系列文章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进步作用了,自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学习》杂志1952年第1期发表了杨耳(许立群)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一文,主张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资产阶级思想;第2期发表了吴江的《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文,把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描写为一种欺骗的手段;第3期发表了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抹杀。这一系列文章是由当时著名的几位理论家连续发表的,他们一致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两面性、积极性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因为长期在上海工作,对资产阶级的行动及其所起的作用有实际且全面深入的了解,冯定力排众议,于1952年3月24日在《解放日报》上,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的文章,对当时理论界普遍存在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左”的看法及实际工作中“左”的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并给予了理论的说明,明确提出“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不是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坚持认为资产阶级还存在一定的积极性。冯定的这篇文章是对上海进行“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切体会,该文送给华东局常委审阅时得到了华东局领导的重视,认为对当前的运动有指导意义,就指示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予以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为当时轰动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冯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此文章,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要有勇气的。
文章发表后,不仅受到了大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称赞了冯定的文章并批评了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部长,写文章的于光远、许立群也是中宣部的,毛泽东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于否定了中宣部的工作,高级党校也间接受到了批评。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1952年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文章),《人民日报》也在4月10日转载了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