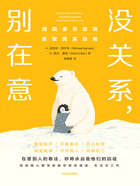
第一部分 FOPO的真相
1 贝多芬的秘密
艺术家永不为囚徒,不受困于自我,不受限于风格,亦不为声名和成就所俘。
——亨利·马蒂斯
没人能真正对FOPO免疫,你不行,我不行,世界级运动员也不行,甚至闻名世界的艺术家也同样为FOPO的力量所阻碍,如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多产的作曲家之一贝多芬。
唯有直面FOPO的力量,我们才能迈出实现自我掌控的第一步。
聊聊贝多芬吧。
对许多人而言,他仿佛是一艘上帝精心挑选的音乐之舰,从更高维度引领音乐发展。他的作品完全改变了古典音乐世界。他打破所有陈规,创造出空前卓越的音乐。他是真正的创造性天才,突破传统,开创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贝多芬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无畏的艺术家之一,却曾有3年的时间生活在恐惧之中,极度惧怕他人的看法。
贝多芬在事业接近顶峰之时,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怀揣着一个秘密,他认为那个秘密一旦泄露,他的职业生涯就会毁于一旦。贝多芬似乎生来就与命运和世界的不公做斗争,而这位极富创造力的艺术家宁愿选择避世隐逸,也无法大声地说出那4个字:“我听不见。”
贝多芬在25岁左右,开始逐渐失去听力。失去他在艺术与生活中最重要的感官,于他而言简直是残酷的讽刺。他迫切地寻找各种治疗方法,从杏仁油耳塞到沐浴,甚至尝试有毒的树皮,却都徒劳无益。最初几年,除医生外,他不曾向其他任何人谈及自己日益恶化的听力问题。他声名鹊起,社会知名度越来越高,却独自带着痛苦和悲伤,困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
为了掩盖听力问题,贝多芬藏在天才艺术家的光环下,伪装成时常分神、沉浸于自己思想的模样。有时,他听不清旁人说话,或听不见别人提到的某个声音,但人们会相信他只是没注意或者太健忘。“我很惊讶,有些人从未注意到我听力不好。或许是我时常恍惚,心不在焉,他们便将我的听力问题归于此。有时候他们说话声音太轻,我几乎听不见,只能听到声音,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但要是有人大喊大叫,我又受不了。天知道我将来会怎样。”[1]
贝多芬忧心忡忡,一方面,他十分担心听力障碍会影响他的音乐创作,尤其是钢琴弹奏能力;另一方面,公众的看法对他也构成了同样强大的威胁。“我如果从事其他行业,事情会简单很多,但在我的行业,这种情况太可怕了。何况我还有不少敌人,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2]他害怕批评者利用这一发现来攻击他。他担心他们的批评导致行业歧视,最终将他排挤出维也纳音乐圈,令他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和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一样,贝多芬也依赖贵族的资助。比起丧失听力本身,克服其可能带来的社会污名或许更加困难。
受到最大威胁的也许是贝多芬的身份。“唉,我怎么能承认自己这一感官上的弱点,我的感官本应比别人更完美。我曾拥有最完美的感官,那是我们行业内都少有人能体会的完美。”他在给他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3]
他是音乐之神贝多芬,音乐之神理应比普通人更能聆听音乐。听觉丧失既不符合他的自我认知,也不符合他的公众形象。他的身份建立在他人的认可与赞扬之上,该身份举足轻重,如同他的血肉一般,真实而不可动摇。奇洛乌斯基亲王是他的资助者,在他写给这位慷慨的资助者的信中,他的身份近乎神话:“亲王殿下!你是谁,是由环境和出身决定的。我是谁,我是我自己。世间亲王成百上千,贝多芬却只有一个。”[4]
面对生存威胁时,我们大多会寻求自保,贝多芬也一样。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向内自省,转变自我认知,而是向外挣扎,试图让外部现实符合他对自我的看法。贝多芬竭尽所能去构建现实,以逃避他人的看法。他常常听不见别人说话,又不敢让他们大声一点儿,唯恐被人发现他失聪的秘密。为了隐藏这个秘密,他扮演厌世者的角色,与世隔绝多年,孤独地活在无声的世界,甚至曾想过自杀。
追求认可
贝多芬自小就深信外界的看法非常重要。他的父亲约翰是一名资质平平的男高音歌唱家,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因酗酒而终结,便想通过儿子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自命为孩子的导师,对年幼的贝多芬施加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不断逼迫他。为了让贝多芬听话,约翰总是对他怒吼,言语威胁或拳脚相加,甚至把他锁在地下室里。[5]有一天晚上,约翰跟朋友出去玩儿,回家后,他让贝多芬为他的朋友演奏。小贝多芬那时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到钢琴键,但他只要弹错一个音,就会遭到父亲的殴打。
年少的贝多芬音乐才华日益出众,于是他父亲决定让他成为下一个轰动欧洲音乐界的人物。约翰扮演起18世纪戏剧舞台上的父亲角色,像做销售一样在德国波恩所有的音乐圈里宣传自己的儿子。贝多芬7岁时,约翰在科隆租下一间礼堂,并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宣传他“6岁的小儿子”有幸为宫廷演奏。[6]为了让贝多芬更贴合神童的形象,约翰谎报了贝多芬的年龄。从幼年开始,贝多芬一直接收这一不算隐晦的信息:“真实的你还不够好。”
在事业早期,贝多芬就意识到,他在19世纪维也纳音乐界的发展与他的仰慕者的地位和意见直接相关。在更深层面上,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唯有表现与成就才能带来认可和爱。他父亲的行为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贝多芬被爱不是因为他自己是谁,而是因为他做到了什么。将爱与认可混为一谈,往往会导致人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形成追求认可的心理行为模式,而身处聚光灯下,又进一步加强了贝多芬的自我认知。
庇护所
唯有一个地方贝多芬可以去,那里别人的意见无法进入,自我怀疑无法侵袭,他的贵族资助者们也无法触及,那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渐渐地,贝多芬完全沉浸于自己的音乐中,消失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彻底遗忘周围的环境,失去所有自我意识。他在任何地方都可能进入这种状态,如在笔记本上乱涂乱画或在人群中即兴表演时。
贝多芬的一位儿时的朋友回忆,有一次,她在和贝多芬说话,但他仿佛心不在焉,根本听不到她说什么。等他终于回过神来,会说:“哦,对不起,请原谅我!我刚刚走神了,我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那想法太美、太深邃了,我实在无法分心。”传记作家简·斯沃福德将贝多芬这样的情况形容为一阵“恍惚”[7],称“他即使身处人群之中,也与世隔绝”[8]。一位对贝多芬早期事业起到重要作用的朋友给他这种状态起了一个名字,叫“狂想”[9]。贝多芬的狂想成了圈内的传奇,当他脱离社交时,常有人说:“他又陷入狂想了。”[10]
在狂想中,贝多芬发展出一种内在能力,即他能专注于音乐,隔绝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干扰。在那里,他能够不在意他人的看法,他享受在自己的洞穴里探险,因为他知道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倾听自己的音乐。
对他而言,艰难的挑战在于从狂想中走出来,重新回到认可游戏中。
直面恐惧
贝多芬的听力问题日益严重,最终到了无法再掩饰的地步。1802年10月6日,他给他的兄弟们写了一封诚挚而痛苦的信,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困境,这封信被称为《海利根施塔特遗嘱》。[11]
哦!这些揣测甚至直言我心怀恶意、偏执厌世的人,你们真是大大地误解我了。你们不明白我为何表现出这个样子……请原谅我,当你们看到我退缩回避时,我内心其实很愿意与你们交往……我只能活得像个流亡者,一旦接近别人,就被恐惧深深笼罩。我害怕自己的病情会被发现……当我身旁的人听到远处传来的笛声,或听到牧羊人的歌唱,而我完全听不见时,这是多么耻辱啊。这样的事情让我近乎绝望,如果再多发生几次,我恐怕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关于改变,最浪漫的情形是我们发现自己身心状态或环境条件的变化,并认识到自己需要做出改变。我们勇于直面改变,敢于承担风险,积极做出改变并收获回报。
不幸的是,这种浪漫难得一见。行为模式根深蒂固,改变谈何容易。我们都知道自己应该改变,但通常要等到迫不得已之时,才能真正做出改变。等到跌入谷底,痛苦已难以忍受之时,我们才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根据我的经验,往往是痛苦迫使我们改变。贝多芬便是如此。
《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是贝多芬身处最低谷时的绝望之作,但它同时标志着贝多芬与社会认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作者之一打开了新的大门,而这并非巧合。在说出自己的绝望后,贝多芬接受了失聪是自己的一部分。他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充分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我可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只有艺术拉住了我,在我完成应该完成的一切之前,我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说,现在我必须有耐心,让耐心引导我,我确实这样做了。”
贝多芬决定暴露自己最大的恐惧,通过这样做,他把自己从FOPO的麻痹控制中解放出来。他写道:“所有邪恶都隐藏于神秘的表象中,在孤独中显得伟大不凡。坦然与他人讨论,反倒令恐惧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只要我们熟悉了自己所惧怕的东西,就感觉已经克服它了。”[12]坦露失聪的秘密并没有毁掉贝多芬的生活,反倒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解放了他。他不再试图控制他人的看法,而是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通往掌控之路
当贝多芬不再担心他人的看法时,他不再为外部世界表演,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为自己演奏。当他拥抱第一准则时,他真正走上了通往掌控之路。
掌控是对内在导向生活的外在表现。掌控之路没有终点线,它是一场浪漫的旅程,关注体验,体会真诚,不断探索,与真理共舞。我们只有下定决心,遵从自己的内心,由内而外地面对世界,才能踏上通往掌控之路。
单是技艺卓越不足以让人真正走向掌控之路。你如果不能认清自己是谁,发自内心地去创作,那么最多只能是优秀的表演者,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师。如果你在挖掘自己内心的火焰之前,总是要先测量周围世界的温度,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释放自己的潜能。
掌控无须比较。与其他伟大的作曲家前辈相比,人们可能会一致认为写下《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前的贝多芬已经是大师级别了,但通过与巴赫或莫扎特比较来衡量贝多芬的掌控程度实在是毫无意义。
衡量掌控程度的基本标准是我们每个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唯有接纳掌控的第一准则,我们才能知道答案。
真正实现自我
贝多芬不再浪费自己的内在能量,也不再试图影响他无法完全控制的外在条件,而是专注于掌控自己所能控制的一切。
他放弃了钢琴演奏师的职业,专注于作曲。当贝多芬放下自己应该是谁的执念时,他才真正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实现自我,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音乐世界。
在生命的尾声,完全失聪的贝多芬写下了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那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维也纳康特纳托尔剧院“指挥”第九交响曲的首演,这是他10多年来第一次重返舞台演出。由于他的失聪,演出实际上由迈克尔·乌姆劳夫指挥,但贝多芬忍不住要向演奏家们展示他心中这支交响曲的风格和力量。他充满激情地指挥着管弦乐队,尽管对他而言,他们奏出的乐曲是无声的。[13]演奏结束时,贝多芬仍然面向管弦乐队,因为他听不见身后观众的声音。女低音歌唱家轻轻拍了拍贝多芬,让他转过身面向观众,接受他们雷鸣般的掌声,以及在空中挥舞手帕和帽子的人群的赞赏。
我们常常试图控制他人的观点及他们对我们的看法,而讽刺的是,因为渴望获得认可,我们放弃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将永远是他们的囚徒。
每日小练习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从而了解自己实际能控制的事物。你可以想象我说的内容,或者用纸笔把它们记下来(见图1-1)。
画一个大圆,再在里面画一个小圆,像一个甜甜圈。在外环里列出在生活中很重要,但你不能百分之百控制的事物。首先是他人的看法,很显然我们对此不具有完全的控制力。还有天气、你支持的球队的输赢、你的上司、市场环境、工作环境等,你可以列出很多。
在中间的小圆里,列出你能百分之百控制的事物,比如你上班到岗的时间、你跟孩子交流的方式、你在工作中的努力程度等。

图1-1 你能控制的和你不能控制的
现在,看看你的列表,什么是你真正有能力控制的?什么是你无法控制的?
[1]引文和译文参见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The Life of Ludwig van Beethoven: Vol. 1 [1866], ed. Henry Edward Krehbiel (New York:The Beethoven Association, 1921), 300。
[2]Thayer,Life of Beethoven,300.
[3]《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是贝多芬于1802年10月6日写给兄弟卡尔和约翰的信,参见http://www.lvbeethoven.com/Bio/BiographyHeiligenstadtTestament.html。
[4]Jan Swafford, Beethoven:Anguish and Triumph;A Biograph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428; H. C. Robbins Landon, Beethoven:A Documentary 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210. Lichnowsky's physician, Dr. Anton Weiser, tells the story of when Beethoven was offended by being asked to play the violin at a dinner.
[5]Swafford,Beethoven,21.
[6]Swafford,Beethoven,53.
[7]Franz Wegeler and Ferdinand Ries, Beethoven Remembered: The Bio-graphical Notes of Franz Wegeler and Ferdinand Ries (Salt Lake City, UT: Great River Books, 1987), 39.
[8]Swafford,Beethoven,98-99.
[9]Swafford,Beethoven,128.“他的天赋之一是狂想,这种能力让他遁入内心世界,超越周围的一切人和事,也超越了无数困扰他的苦难。他在钢琴键上即兴演奏,甚至在同伴中也能找到孤独。”
[10]Swafford,Beethoven,98-99.
[11]《海利根施塔特遗嘱》。
[12]David Ryback,Beethoven in Love(Andover,MA:Tiger Iron Press,1996).引自贝多芬1817年的作品。
[13]Nicholas Cook,Beethoven:Symphony No.9(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