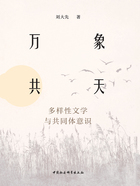
一 本土理念:历史与经验
前现代中国的政体形态、典章制度、族群构成、地理疆域经历起承转合,关于“中国”内涵与外延的认知也屡经变异。秦汉分别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度量衡、文字和行为规范,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整合等方面,建构起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大一统”王朝帝制观念与治理方式,应对地理、人口、文化风俗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原则,“量地制邑”与“分民而治”“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相结合[2],除了直接统辖,还有和亲、结盟、羁縻、朝贡、土司、流官等多种治理技术与操作。这种“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的辩证,成为处理帝国文化多样性的有效理念,在维护统一与连续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追溯其渊源,显然是从先秦元典中而来,它们构成了天下式世界观中经久不衰的精神遗产。
《诗经·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在这种世界观中天子的疆域没有外部与边界,显示出文化先发地带极大的文化自信;因而在对待他者时也有包容并举的气度,如同《论语·颜渊》所说:“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4]所谓“四海”从地理结构上来说,处于“中国”(实际地域就是九州)之外,是从华夏中心一层一层往外推延的所在。《尚书·禹贡》勾勒了这种外推图示:“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脩,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只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5]“五服”(甸、侯、绥、要、荒)沦漪般地扩大结构,是西周重要的邦国畿服制度,后来也有三服、六服、九服的不同划分,大致从“要服”开始已经不是自己人了,清人江声注“要结好信而服从之”[6],基本算是称服的友邦;其中的“夷”孔安国注:“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荒服”《史记集解》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有着因俗而治的自治意味,而“流”则是“流动无定居”,属于化外的游牧族群。这种沦漪模式以关系的远近亲疏扩展,类似于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7]王柯曾将先秦天下观念归纳为“三重的天下”:理论与现实中的“四海之内”与“九州”,阶级制的“内服”与“外服”,“中国”与“四夷”的有机统一,[8]颇为精当,但“阶级制”的提法则属后设叙事,用“亲疏制”可能更符合彼时的理想类型。
“中国”之外的“四海”是边缘族群及其生活区域和习俗文化。《尔雅·释地》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瓠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9]《风俗通》解释:“夷”,“东方人,好生,万物抵触地而出。夷者,抵也”;“蛮”,“慢也。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慢”;“戎”,“凶也”;“狄”,“辟也,其行邪辟”[10]。三国时经学家孙炎解释“海”为“晦,晦暗于礼义也”。可见,“四海”并非单指地理概念,与“中国”一样,更多是文化概念。“中国”的华夏与“四海”的蛮夷戎狄,形成了五方之民,因为气候、地理、风俗、文化的差别,而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礼记·王制》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11]这段话经常被引用,因为它确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同族群的相处模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而成为此后处理族群关系灵活机动原则的滥觞。需要注意的是,器物、服饰、饮食、气味的差别,成为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但茹毛饮血、披发文身、生食穴居、气味腥膻这些外在因素,并不构成种族主义式的排斥,而存在着接受教化而转化的可能,“和而不同”的终极目标当然是“天下大同”,但在理想状态达到之前并不妨碍“求同存异”。
本书并不意在阐释此种类似“文化民族主义”的观念,相关讨论已经很多。我想指出的是,“夷夏之辨”“尊王攘夷”之说固然显示出某种华夏中心主义,但“中心”并未固化不变,而“夷夏变态”的交流也从未停止过,而是双向互化:一方面是因利乘便、顺势而为,如墨子论“节葬”时所言“便其习而义其俗者”[12];另一方面则是趋利避害、经变从权,如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华夏礼乐所构成的文教叙述,如果换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类比为文化话语权和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正是因为有主流文化强大的实力与价值观的向心力,才造成了后来历史进程中“华夷一体”的可能性,为现代的“中华民族”塑造奠定了基础。这种情形在中原王朝衰落、游牧民族南下的碰撞与交流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国力强盛的年代,文化中心的强盛足以使之具有巨大的兼容、吸附与转化的力量,“夷夏之辨”往往隐匿不显,凸显的是胡汉一家、华夷一体,如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3]只有在面对周边民族威胁之时,“正统论”才会浮出水面,如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宋契丹辽金西夏并立,这几个动乱冲突年代,正朔、服色等问题才会成为政治和文化精英比较关注的问题。[14]从历史发展来看,夷夏之间的界限始终在绝对与相对之间游走,展现出不同的立场与抉择,引发不断的融合与创变。
在这个意义上,元和清这两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在中国历史转折中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们都在军事开拓和疆域扩展上留下了现代中国继承的广袤地域;更值得探讨的是,元使得汉地与江南的融合,清对西藏、新疆(包括西域与西南)的囊括,以及游牧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甚至中亚色目人、东北亚的朝鲜、俄罗斯等族群也合并入中国族群的谱系中来,“小中国”由此走向了“大中国”。元、清两代其实都实行过民族歧视政策,因而也在后继的明朝和民国肇起之初引发带有种姓之别与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拨,但冲突融合的结果是“中华民族”观念的生发和拓展。如萧启庆在谈到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影响时所说:“中原文明在蒙元时代虽经历空前严峻的考验,却能浴火重生,而且并未偏离原有的发展主线。在蒙元覆亡之后,中原文明的核心特质如儒教国家、君主专制、官僚组织、士绅社会、士大夫文化以及以汉族为中心的族群结构等皆无根本的改变。……元朝亦是以中原为政治中心不再是一个草原国家。忽必烈及其继承者虽号称为蒙古世界帝国的‘大汗’,但为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不得不以中原的正统帝王自居,因而必须尊崇中原的典章文物,照顾臣民的生活福祉,对中原文明未曾过度摧残。”[15]与某些带有殖民时期“满蒙史学”色彩的论述中强调元的蒙古中心世界帝国意味(比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一系列论述)不同的是,从成吉思汗的大帝国到忽必烈的元帝国,虽然都堪称世界帝国,但忽必烈之后,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文化,都还是归入到了中国的正史系统之内[16],主流文化的涵濡化育,使得元朝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国的重要发展阶段。[17]
清更是成功地将汉满蒙群体为主的内地—东北、内亚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藩部、改土归流后的西南“新疆”联为一家,多样性的疆域、经济、信仰、语言、文化在因地制宜的政策中得以协调。日本和美国的新清史学者乐于强调清帝王的“共时性君权”(simultaneous emperorship)或“复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y)式的特点,即认为在皇帝身上聚合了应对不同地区与族群的族长、大汗、活佛、皇帝、东亚共主等不同形象,因而建立起不同的法理关系。在这种论说中,清朝与此前汉人王朝不同,其同一性是非制度的同一性,甚至“满洲特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18]但这种说法忽略了此前唐朝就有“天可汗”的称号与认同[19],无疑本末倒置,忽略了主流[20]——因为清王朝要接续正统,无论从功利考量还是从文化权衡,要完善稳定的统治,都必须认同主体文化观念。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雍正要证明清朝合法性的《大义觉迷录》[21],延续的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且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22]“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五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23]华夷一家、无分内外说明对正统价值观的接续,到了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他们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所以在高宗看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方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正因为如此,高宗才会旗帜鲜明地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24],甚至较之一般士人的认同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方、族群、宗教组织在清帝国的联结,形成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与文化基础,清帝似乎带有“复合君主”色彩,但从制度到观念,族性文化因素始终只是支流,而主流的则是先秦以来的正统观,“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25]。这是维持了中国二千年“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