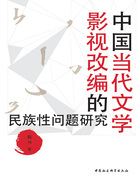
第四节 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红色经典“抗战”小说及改编影视剧中的妇女与民族国家
从本质上说,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对立的,前者强调女性自身的利益与价值,反抗男权和父权压迫,而后者强调女性对民族国家的牺牲和贡献,在经典女性主义者看来,国家民族主义是“父权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压抑与暴力之源”[70]。但是,二者的关系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还是不一样的,卡普兰认为“在欧洲,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是反常的,不寻常的……而亚非地区的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是在男性民族主义者的启蒙、倡导、鼓励下出现的,民族主义支持和领导妇女运动,所以双方的关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合作和从属关系”[71]。
抗战时期,救亡图存压倒一切,民族主义成为战时中国的强势话语,女性主义完全是依附和从属于前者的,即使是根据地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和西方女权运动的主旨不同,而是“带有战前民族动员、战后整合重建时所需的妇女劳动力的意图”[72],仍然是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宏大体系之内,并且与阶级斗争话语紧密相关。建国初期的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由于其作者的男性身份、时代政治文化背景和抗战题材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其男性、阶级及民族主义的话语立场,在这些作品中,民族主义压倒一切,女性主义配合和服从。其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基本都是为民族国家隐忍、奉献与牺牲的角色,以自身的被动、犹豫、情绪化衬托正面男性的主动、果敢与理性。而反面女性则是以被否定的身体来说明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特质的摒弃。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见抗战时期中国北方农村妇女为民族国家所做出的超越男性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包括情感的与身体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批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抗战”小说社会史意义的一个层面。
不过,值得提及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部分“抗战”小说比如《苦菜花》中,民族主义并非将女性主义挤压至无,而是或潜隐或曲折地表现出了对母性与女性特质的同情与尊重,这些符合女性主义立场的表述恰是小说被视为具有人情人性、可读性并能成为经典流传的因素之一,却在特殊时期的政治语境下因其与民族主义和阶级话语的霸权相抵牾遭到了批判。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批“抗战”小说自问世以来,不断处于被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之中,通过改编而实现“熟知化”的过程也是经典得以成就的一种途径。改编后的影视剧作为原小说的“互文本”,与原著存在着相互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具有不同于原文本的新的意义和价值。就民族主义的压倒性地位来看,改编后的影视剧包括新世纪以来的影视文本一如原著,甚至还有所强化。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表现为民族主义+阶级斗争话语的加强组合,而新世纪的影视剧则表现为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组合,它们共同的缺憾是少了原著中对女性的理解与同情之处。前者是受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环境影响,而后者则受当下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大众传媒娱乐化倾向的共同影响。而创作于建国前后的原著小说由于创作者自身就是抗战历史的亲历者,其作品多具有真情实感和著史的求真意识。比如冯德英自身就有一位投入抗战后勤工作的母亲,其小说《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来自于他对生活中真实的革命母亲的体验与观察。这与后来影视剧中观念先行的想象的母亲自然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由上述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因为阶级话语弱化,反面女性形象与原著相比发生了较多的变化。
本节接下来将从民族国家视野中女性的几种不同角色定位来分析红色经典“抗战”小说及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中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一 作为劳动力与战斗力的女性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与家庭的理论,将女性从封建家庭中解放出来,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投身围绕抗战中心的各项社会运动,更是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解放运动对妇女劳动力与战斗力的需要与依赖。从这点来看,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晚清以来维新思想家包括梁启超等人的妇女解放思想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后者提倡妇女解放身体、接受教育、拒绝早婚等其实还是为了强国强种,辅助男性参与挽救或建设民族国家。解放了的女性身体被民族国家最大程度地利用,成了抗战时期重要的劳动力和战斗力。然而,女性在获得社会性的同时,有时会丧失了部分生物性,相较男女体能存在的天然差异,女性付出的代价其实更大。从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出妇女为抗日工作所付出的巨大体力劳动:“1943年太行第七专署,有30000名妇女纺织,生产土布500万疋,得工资粮200余万斤。这不仅对占胜灾荒起了重要作用,还促进了消费、生产合作带来的发展。”[73]1940年7月制定的《太行军区的组织及其工作纲要》规定,20岁至40岁之妇女,均应参加自卫队。这些女性在自卫队中的作用和男性一样,负责铲除汉奸、肃清敌探、破路拆堡、空舍清野、救护伤病员等。[74]如果说救护伤员、织布生产还与女性的生理体能相适应的话,“铲除汉奸、肃清敌探、破路拆堡、空舍清野”等重体力任务则显然更适应男性。
在否认男女两性生理差异方面,西方女性主义的某些流派和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不过,前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差异的消除实现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话语地位,旨在女性自身权利的主张和主体性的实现。而后者则是基于阶级斗争理论反对一切强势力量对弱势力量的压迫,包括男女体能的差异,目的还是为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建设服务。然而以消除男女性别属性差异为代价的两性平等是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的不平等,正如美国女性伦理学家艾莉森·贾格所说:“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两性间的差异是显著的、无法逃避的。当这些差异在两性形式上的平等的名义下被忽略时,男女之间持续的、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便会被掩盖、被合理合法化。”[75]
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中出现了较多的革命女性形象,而且用较多篇幅表现了山东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比如娟子冲破家族封建观念的束缚参加革命工作,花子摆脱作童养媳的悲剧命运追求自由恋爱。这些围绕妇女家庭生活进行的斗争本质上还是为了让妇女走出家庭参加抗战工作,服务民族国家。解放了的娟子和花子都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当地的妇救会长。如果不反封建,不反家族势力,就无法更好地胜任妇救会长这个职务。妇女救国会是抗战时期中共为了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而在华北各根据地成立的妇女组织,其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使农村妇女摆脱男权压迫、恋爱自由等,更重要的是组织妇女参与上述后勤工作及至抗战一线中去。所以当后期妇救会的工作挑战传统乡土伦理、影响抗战大局稳定的时候,“中共不得不转变妇女工作的方向,将‘性别革命’让位于‘阶级革命’,使得妇女作为性别的利益被搁置,甚至最终被放逐……就实际而言,中共在民族、阶级利益面前暂时搁置了女性的利益,并将女性的解放最终依托于民族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上”[76]。
或许由于深受母亲影响,尽管冯德英小说《苦菜花》的主要立场是男性、阶级和民族的,但仍有潜隐的超越上述阶级话语的对女性的同情和尊重,这和当时其他“抗战”小说尤其是代表绝对男权话语的《吕梁英雄传》有着鲜明的区别,这也是该小说在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所在,比如小说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叙述方式,表现并肯定正面女性作为女人与母亲的自然属性,在中性女性身上寄托超阶级、超功利的性爱等。
《苦菜花》对上述抗战中女性体能的巨大付出是有着真实的再现和同情的。小说中的女性如母亲、娟子、花子、星梅不仅承受了支援抗战的繁重的照顾伤员、后勤生产、铲除汉奸、肃清敌探等任务,甚至还亲历对敌斗争一线,承受了斗争中来自男性敌人的肉体折磨与摧残。其中有一段关于娟子在山里走夜路遇袭的描写,袭击她的是特务宫少尼,后者是男性,二人没有用任何武器,全部是肉搏,虽然娟子作为主要正面人物在这场搏斗中最终是胜利了,但作为女性的体能局限还是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出来,最后当敌人倒下的时候,她也昏迷倒下了。叙述者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写这场艰难的搏斗,应该是注意到了女性体能与男性之间的差异,不过为了掩饰这种差异,他做了一些解释:“凭娟子那从劳动中锻炼出来的强壮身体,力气是大于敌手的,她大多是占着上风,将宫少尼压在身底下。可是一来娟子中午只吃点冷干粮,晚上还一点没吃,再加上走了这么多山路,渐渐身子在发软,有些无力了。”[77]
1965年的电影《苦菜花》和2004年的同名电视剧则明显回避了对上述战争中女性体能和男性体能比较的问题,它们对男性反派人物的描写较小说更为脸谱化,旨在将作为敌人的男性塑造得不堪一击或更加猥琐。电影《苦菜花》是受时代的阶级斗争话语影响,其中,娟子只稍微搏斗了几下,便拿出了枪,然后宫少尼便狼狈逃走,娟子开枪击中了他,获得完胜。电视剧《苦菜花》中打斗也很简单,但突兀地加进了宫少尼露出淫笑试图强奸娟子的场面,就将小说和电影中民族和阶级对立的搏斗场面变为具有性的意味的搏斗场面,反映了当下影视剧迎合受众感官娱乐的倾向。同时,与电影中一样,娟子最后制服宫少尼也是依靠枪,武器的运用遮蔽了男女体能的差别,可以使女性轻松地制服男性敌人,明明在搏斗镜头中看见娟子并没怎么吃亏,后面镜头一切换,居然就是娟子貌似重伤的躺在了床上,这自相矛盾的镜头是电视剧既想保留小说中娟子重伤的情节,又忽略了搏斗场面中男女体能差异并且将敌人弱化处理的结果。
实际上,后来的“抗战”影视作品对女性在抗战中的劳动生产和实战搏击表现得远不如小说充分,或是因为篇幅限制,或是编导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以娱乐为创作目的,大大增加复杂情感戏份挤压生产劳动情节,以武打神技简单化残酷的战争搏击,从而削弱了剧作的历史真实性。2005年的电视剧《苦菜花》如此,同时期的电视连续剧《平原枪声》也如此。比如剧中马英母亲变身成了身怀武功的红枪会的成员,一把年纪可以轻松轮棍打倒几个壮年的身为职业军人的鬼子。小说中那个默默奉献作好后勤工作支持抗战的民女云秀,在电视剧中居然变成了一个整天想着嫁给马英甚至不惜做小的“花痴”一般的女性。在后来的“抗日神剧”中,女性们也是靠着不着思议的武术绝技神一般地制服一群男性敌人。
上述影视剧中无论是赋予女性武器或神功,都是旨在遮掩女性在战争中体能与男性的差异,无法真实再现抗战历史中参与实战的女性在肉体上承受的重荷。同样,将女性弱智化为一心只想着嫁人的形象同样遮蔽了抗战时广大农村妇女在后勤保障方面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样,小说中作为劳动力与战斗力存在的女性,在后来的影视剧中被意识形态或大众传媒神话重新建构,成为想象的失真的符号,既没有再现符合民族主义召唤的女性价值,也没能正视男女两性身体的真正差异从而实现对女性的同情与理解。从这个角度说,某些新世纪的“抗战”影视剧甚至不如原著小说,因为后者虽然是民族主义的,但还是客观再现并高度认同女性在抗战中的体能付出的,前者则纯粹将女性定位为娱乐受众的角色。
二 作为母亲的女性
在民族主义者想象民族的文化符码中,“母亲”是个重要的词语,比如“大地母亲”“黄河母亲”等,这些女性化的修辞旨在强调“由母亲所象征的民族包容性、保护性、孕育性,以及与大自然结合的无穷力量”。[78]同时,在抗战时期,“母亲”这一文化符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代表着战乱时对伦理亲情聚合的情感依归,一方面还代表着养育为国尽忠的子女的奉献者和牺牲者。红色经典“抗战”小说多有母子或母女的叙述主线,呈现出的即是上述民族主义的文化内涵。
在小说《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中都有一个子女从事抗战工作、苦盼家人团圆的母亲形象,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母亲的心情,包括年节时渴望儿女归家,以及希望儿女早日成家,这些都是属于宗法社会的人伦常情,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一是用来反映战争对传统人伦的破坏,二是用来反映革命者弃小家为民族的家国大义,同时也能反映乱时游子的情感依归。
当然,更重要的是,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的民族主义话语对母亲的定位还在于后者为民族国家的奉献和牺牲。母亲的自然和生物属性及传统文化对母亲角色的定位是对子女的保护、对家的守护,然而民族战争往往要求母亲牺牲这种自然属性,成为符合民族主义话语要求的“英雄母亲”。也就是内尔·诺丁斯在《女性与恶》一书中所说:“然而矛盾的是,女人竟也允许自身去支持某些施加苦难的行为,特别是对于被认为有必要为了一种珍贵生活方式所发动的伟大战争的赞同。女人们有时还会因其儿子的捐躯表现得格外骄傲,这是一种男性主导的民 族——国家勇气的姿态。”[79]这是“同女人基本的保护工作极不相符的姿态”。[80]从这一点上看,红色经典“抗战”小说中的母亲基本都属于牺牲者的形象,不是牺牲子女,就是为了子女所从事的国家民族大业牺牲自己。《苦菜花》中的母亲为了保护兵工厂的信息而不得不牺牲小女儿嫚子的生命,其他的儿子和女儿也参加了革命,随时有生命风险。《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小说中都有一个儿子参加革命随时担着心并且支持着儿子的事业自己付出代价的母亲。这样的母亲是民族国家话语所嘉许的,自然也是为小说作者所肯定的。
值得肯定的是,尽管上述小说中的母亲都是牺牲者形象,但小说并没有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将母亲塑造成完全失去生物属性的纯粹的脸谱化形象,而是反映了母亲内心潜意识深处的“保护”意识:保护子女,维系母子之间源自生物本能的情感纽带。所以小说中作为牺牲者的母亲经常处于纠结的复杂状态之中。小说《平原枪声》中的马英母亲尽管后来在敌人面前表现非常勇敢,但她之前并没有让儿子当兵的想法,总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当儿子参加革命后,她无奈,为儿子担心,“娘不是不愿意你工作,娘恨不得你把这些黑了心的都除掉,可你娘跟前就你这一个命根子啊!你要是有个好歹……”[81]。小说《苦菜花》中的母亲也有类似的心情:“母亲很幸福地看着安静地睡在她身边的儿女们。是的,她现在是最幸福了。孩子们像一群小鸡,经过几天的离散奔波,又回到她的身边,她随时可以看到他们,爱抚他们……她心里非常满意地想:就这样永远永远地在一起过下去吧。谁也别再离开她一步吧。”[82]这是一个自然的母亲。当她面临女儿嫚子被折磨时,内心并不是大义凛然、意志坚决的,自然的母性不断地在与阶级性与民族性做斗争,所以,母亲的内心活动相当复杂,她有过恐惧:“母亲虽早已料到这一层,但当听到后,还是抑制不住那巨大的内心恐怖,她开始哆嗦起来,身子无力地靠在椅背上。她知道,她虽有一颗做母亲的为孩子可以掏出来的心,可是她已经被折磨得稀烂的衰弱不堪的身体,怎么能保卫住孩子呢?啊!不能丢弃孩子啊!孩子是她的命根子,她的一切!哪个做母亲的能眼睁睁见孩子被杀死而不救呢?!不,决不能!”[83]有过幻想:“用做母亲对孩子的疼爱心说出最挚诚的言语,能打动这些也是人的东西发发慈悲吧?”[84]甚至一度想屈服:“她要屈服——赶快饶了孩子吧!不,不能。”[85]这并不引人注意的四个字“想要屈服”是有血有肉的,但有损于民族主义英雄母亲的决绝形象,所以在后来的影视剧《苦菜花》中,是从来不曾出现在母亲思想中的。
上述“母性”的保护本能实际上是追求和平与反战的,反映了身经战乱的作家对和平生活、伦理亲情的一种渴望,比如小说《苦菜花》的结尾就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团圆聚合场面:丈夫、孩子们包括下一代都聚在了母亲身边,女儿秀子还拿了一束鲜花给母亲作为生日礼物。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中的文化女性主义思想肯定女性的母性力量,包括珍视生命、保护弱小等,激励了众多女性投入到社会改良和反战运动中,其中代表性的思想家简·亚当斯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主义者[86]。小说对“母性”的肯定契合了文化女性主义的思想,却与民族主义对“英雄母亲”的叙述不符,所以到了1965年,由于政治形势变得更严峻,此时上映的电影《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与小说原著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阶级觉悟和革命性变强,自然母性消退。小说中是儿子主动向母亲表示想参军,当儿子跟着队伍走的时候,母亲是纠结不舍的,所以她想最后摸儿子几下,对他再说几句话,然后流下了热泪。而电影中则是母亲主动送儿子参军,她目光坚定,拉着目光茫然的儿子的手对八路军同志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们”。对方问:“兄弟小,你舍得?”母亲微笑着点头说:“舍得,鬼子财主不怕穷人哭,怕的是枪。”这个决绝坚定的微笑着主动送子上战场的母亲作为英雄母亲的形象彰显了前述“男性主导的民族——国家勇气的姿态”。电影为了进一步减弱母亲的自然属性从而强化其革命性,又改编了一个重要情节:让母亲的另一个儿子德刚变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纪铁功,塑造了一个不太真实的巧合,当纪铁功牺牲的时候,母亲才发现他是自己早年离家的儿子,没有什么激烈的情感表示,只说了句:“他为了穷人得救,舍命,值得”,这里母亲的阶级属性完全压倒了自然属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21世纪初,由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恶化,“抗战”影视剧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强,剧中母亲的革命性也是相较原著有所强化,自然母性则弱化。1999年电视连续剧《敌后武工队》甚至为主人公魏强设置了一个原著中没有的母亲,这个母亲只是一个为了儿子事业牺牲的角色,同时其牺牲作为家仇进一步强化民族仇恨。2001年电影《平原枪声》中的母亲则没有了小说中人物对儿子细腻不舍的感情,在剧中几乎没说几句话,在被捕后及在狱中见到马英时,除了几个短暂的镜头,没有任何的语言。可见母子情不是该片重点表现内容,母亲仍然只是一个受害的体现国仇家恨的符号。2010年的电视剧《平原枪声》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思想有较多表现,同时还带有“抗日神剧”的色彩,主人公马英的母亲宗法意识很强,总是在逼着儿子娶亲,为的是让马家有个后,说一不二,不让儿子违背她的意志。这个宗法性的母亲已经完全不似小说中那个认为能“守着儿子做活,看着儿子安心地入睡”就是做母亲的一种最大享受的母亲。后者的感受源自母亲的天然属性,前者则是被文化建构的。所以这个宗法性的母亲在儿子面对生死危境的时候,想的居然不是母子的分离,而是说“生死没个谱”,希望儿子赶紧生个大胖小子。同时这个母亲还是民族主义的,在狱中见到儿子时,她的台词时:儿子,你一定要活下去,要抗日。而原著小说中的母亲只是激动地说了句“孩子”便热泪盈眶,“心碎了,头蒙了”,然后昏厥了过去,并没有让儿子坚持抗日的大义凛然。2004年的电视剧《苦菜花》依然沿用了上述1965年电影中的巧合情节,表现出较强的民族国家话语色彩。母亲在面临女儿嫚子被敌人折磨时,虽然也有如小说中一样的痛苦,可是却少了小说中的纠结,更不曾有小说中想有屈服的一闪念。所以电视剧的结尾是母亲又把另一个女儿秀子送上了战场,而且整个家庭是处于分的状态,这个结尾也和1965年的电影一样。如果说原著小说的其中一个主题是表现民族国家话语压力下的母性与母爱,在电视剧中这个主题几乎淡化为无了,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娱乐化色彩的男女感情纠葛:革命母亲居然和反面人物财主少爷王柬之有暧昧情感,而且这情感还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
三 作为女人的女性
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的话语系统基本是男性/民族国家视角的。所以在性别叙事上,存在着不平等的二元关系:一方面在小说中对女性身体的叙事远多于男性身体,另一方面则将女性在男女关系中表现得本能、情绪化,而男性则表现为清醒理智。后一点也是西方二元对立话语常见的一组范畴,也是女性主义者想要反抗的加之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1.被凝视的女性身体。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的作者虽然都是男性,但他们的小说随处可见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包括外貌、声音和体态打扮。这些身体描写其实是男性视角、阶级意识、道德准则杂糅之后的想象的产物,所以存在着模式化、刻板化的倾向。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所说:“身体有其永恒的公共的一面;我的身体在公共领域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构成的,它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身体从一开始就被给予了他人,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并在社会生活的严峻考验中得以形成。”[87]小说中关于女性身体的描写是按照阶级性进行区分的。对无产阶级阵营的女性都用正面评价的词语,地主阶级的女性基本都用负面评价的词语。将人物相貌的美丑与阶级及道德范畴相关联的写法曾长期流行于中国当代小说及影视作品中,只是在红色经典作品中表现得比较突出。首先,小说中无产阶级女性的肤色基本是黑或者红,比如《苦菜花》中的娟子就有着“被太阳晒成黑红色的方圆开朗的脸庞”,这种肤色属于年轻的劳动女性,应该是基于小说作者对现实生活中此类女性的观察体验,也反映了作者对劳动的、健康的肤色的赞赏。而地主阶级女性的脸色则是不健康的黄色,比如《平原枪声》中的地主婆建梅娘则被描述为“黄脸婆”,《苦菜花》中汉奸地主王竹的妹妹也是“蜡黄的脸皮”。其次,无产阶级女性是自然不加修饰的。这些小说中没有一处对无产阶级女性修饰妆容的描写,反过来,地主阶级的女性一出场,全都是精心妆扮过的,包括擦粉、烫发、使用口红、穿旗袍等。作者们对女性妆容修饰的反感倒不是如西方女性主义者那样反对女性特质对女性身体的束缚,而是基于传统道德、乡土立场对城市时尚文明的反感。所以他们将这些修饰手段多安排在反面女性身上,并且使用负面倾向浓厚的词语来进行丑化,比如冯德英的《苦菜花》,其中写王竹的妹妹玉珍:“她那蜡黄的脸皮也没因擦上浓粉和胭脂好看一些,相反倒和耍傀儡戏的石灰人差不多,更显得丑陋而阴沉。”[88]《平原枪声》中地主家的女人红牡丹出场时也是“抹着粉,画着眉,涂了口红,穿一件花旗袍,还特地用火钳在头发上烫了两个卷子”[89]。《敌后武工队》中的汉奸妻子二姑娘也是“一吃饱肚子,就擦胭脂抹粉、描眉点唇地打扮自己”。[90]她的妆扮在叙述者眼中也是“妖艳”的:“二姑娘今天打扮得特别妖艳:身穿一件刚过膝盖、小开气、卡腰的月白大褂,肉皮色的高靿丝袜子,套在她那白白的大腿上,脚下穿着一双皮底的粉缎子绣花鞋……脸蛋涂了很厚的一层官粉,眉描得又细又弯,唇点得又红又艳。”[91]“妖艳”或“娇艳”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异常艳丽而不端庄,显然已经不是对女性形象的客观描述,而是含有传统道德负面评价的信息。在传统伦理道德的话语范畴中,关于女性外貌的正面评价通常都是指向掩饰女性性征的特点的,比如端庄,多是指向女性身体的较少暴露、修饰及情感的较少流露,实际是宗法社会对女性性征的压抑。不端庄也即“妖艳”一词具有性的暗示,代表了女性性征的外露和张扬。除了外貌,反面女性的声音也是非常具有女性特质的,比如“娇滴滴地叫道”(《苦菜花》中的淑花),“娇声娇气地跟着哼道”(《苦菜花》中的玉珍),有的作者则直接用了负面的词汇来形容她们的声音,比如“浪言淫调”(《平原枪声》中的红牡丹),“骚荡的狂笑”(《敌后武工队》中的二姑娘)。
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要消泯女性自然属性的,也即女性特质。希望女人作为像男人一样的战斗力,献祭子女给革命事业,这样的任务是不太需要女性存在被男人欣赏的性征的。所以作者将他们对于女性性征的想象都投射到了反面女性身上,并解释为“淫”的属性,从而使自己的描写有了合法的政治外衣。以此我们可以理解冯德英在《苦菜花》中有大段对于淑花身体的大胆描写:“淑花躺在红花鹅绒炕毯上,高高的胸脯戴着一个水红色的乳罩,一件紫色小裤衩,紧紧绷在她那肥腴的纸一样白的屁股上。她像一只白色的大鹅一样,躬着腿躺着,起劲地抽着鸦片。王柬之紧靠在她身旁,身上仅穿着短裤,一只毛茸茸的长腿搭在她的大腿上。淑花用在烟台跟着妓女和日本军官太太所学来的技能,吸足一口烟,噘噘鸡腚眼似的小圆嘴,向空中一吹,就出现一个团团转的烟圈圈。王柬之对准烟圈吹一口气,一条烟丝从圈里钻出去。淑花吃吃地笑着丢掉烟,爬到王柬之身上,搂着他的脖子,在他嘴上咂地亲了一下,娇滴滴地叫道。”[92]这段描写放在那个时代来看是相当香艳露骨的,而且除了用来表现汉奸女人的淫荡外,并无多大的情节意义,或许暗喻了男性作家对具有性吸引力的女性身体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从潜意识的角度,已经不完全是民族的阶级的视角,而是一种男性的凝视。实际上,《苦菜花》堪称一部女性小说,其中充满了对女性身体、心理的描写,只不过受制于时代环境,女性性征没有明显地体现在正面人物身上,只是隐晦地有所提及,比如提到发育了的娟子“高高丰满的胸脯”,点到为止。倒是在反面人物身上,作者可以充分发挥对女性性征的描写,然后在一个中性人物身上,公开表达了对女性美的赞赏,这个人物就是杏莉娘,王柬之的妻子,论阶级成分,她属于地主阶级,按照刻板印象,她应该被丑化,然而作者将她设置为一个地主家庭内的受害者,并且最后坚守住了民族大义,所以在她身上可以直白地表达作者对女性的赞美:“她虽是三十几岁的人,可并不显老,她还很漂亮,太阳很少晒到她那白嫩细腻的皮肤,她有着蛋形匀称的红晕脸孔,在月牙儿似的淡淡眉毛下,藏着一双细眯着的秋波闪闪的眼睛,她那袅娜的身躯,突出的胸脯,纤细的小手,就连前额和眼角上细细的条纹,在表弟看来,都是故意生出来迷人的。”[93]如果说在正面人物身上,作者不敢大胆表现女性性征(后来几次修改版本,删掉的就有这方面内容),在负面女性身上出现的女性性征又伴以负面评价,只有在杏莉娘这个中性人物身上,作者才能得以真实地表达他对女性身体、女性魅力的欣赏。
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反面人物二姑娘身上也体现了作者对女性性征的认同和审美,尽管如上面提及也有“妖艳”“骚荡”等负面词语,但下面这段描写却客观如实地表达出了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的美:“她二十四五岁,个不高,体不胖,腰儿挺细,黑黪黪的一张小圆脸上,安着两个让人喜爱的小圆眼。两片子小嘴唇,说起话来呱呱的,像爆竹似的那么清脆,哄得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男人,都愿随她的手指的转动来转动”[94],如同上面的杏莉娘在宫少尼的眼里是迷人的,这里的二姑娘在年轻男人眼里也是迷人的。《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实际在不经意中肯定了女性和政治立场无关的身体之美,所以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过多贬低二姑娘,这也为后来以之蓝本改编的诸多影视剧中的具有民族主义立场、改头换面成为正面人物的二姑娘形象提供了基础。
2.被压抑的性爱。性爱是与民族国家话语无关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在红色经典“抗战”小说中,正面人物的性爱是明显压抑、屈从的。只有作为民族国家敌对人物的鬼子汉奸才放纵性爱,表现出前面所述“淫”的特征。作为男权话语为主导的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男主角往往是民族国家的化身,在男女关系上掌握着主动权,为革命事业和民族大义能主动放弃个人性爱的追求,表现出理性的力量,而女主角则是被动的,对性与爱的渴求偶有表露,很快就被民族国家的代表——男主角扑灭,或者在对方的感召下自我压抑下去,表现为感性的冲动。比如小说《苦菜花》中,星梅和爱人纪铁功因为工作分离多年未见,见面后,两人出去散步,听到孩子们唱歌(其中有一句是“她得的是相思病”),星梅夸孩子们唱歌好听,纪铁功马上说“害这种病的人可真不少,就是在艰苦的战斗里也不是没有啊”,星梅被他说中了心事,马上转移话题,让他谈谈工作的事,这时纪铁功开始高谈阔论,大谈兵工厂的事情,期间星梅“那埋藏在心底很久的深情又涌上来……她那长圆形的脸上泛起一层桃花似的赧晕”[95],然后暗示纪铁功希望现在就能成亲,纪铁功抱住她,“他感到她的脸腮热得烤人……他觉得出她的心在猛烈地跳荡”[96],这里的激情全是纪铁功感受到的来自星梅的,而纪的表现则是“沉默使纪铁功冷静起来,他找到克抑炽烈的情感的力量”[97],然后他教育了一番星梅,表示“我不能把你推到一个普通妇女的地位,我们都要在斗争的最前线战斗啊”[98],显然其意指革命女性是不能有普通妇女对性与爱的追求的。这时的星梅哭了,并且忏悔“是我一时糊涂……可是我一见你,心,心就忍不住了……是我不对,我对革命工作想得太少”[99]。
小说《平原枪声》中的建梅一直暗恋马英,但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不被马英接受,这里表现出马英的政治立场胜于男女私情。当她救了马英,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马英却说欢迎她出来参加抗日工作,这种不谈感情只谈工作的态度已经让建梅感动的流下热泪了。当建梅即将牺牲的时候,马英眼中的建梅不是一个女性或恋人,而是一个被捆绑着即将就义的英雄,所以“她的身体像突然变得高大起来,顶向天空”[100],而建梅看马英,则是一个女人看心爱的男人:“啊!他还是穿的那件小白布衫,是她帮他洗了又缝,缝了又洗,不知缝洗过多少次啊!现在它上面滚满了尘土,已经变成灰色了,肩上挂了一个大口子,袖子脱下来,露出他那黑红的肩膀。他那从不变样的脸,也显得消瘦了,浓浓的眉毛拧在一起。”[101]前者视角是政治的,而后者视角则是情爱的。
红色经典“抗战”小说中正面女性的性爱是被压抑、控制的,反面女性的性爱则被表现为负面的“淫荡”,正常自然的性爱只能体现在一些中性人物身上。后一点,只有小说《苦菜花》做了大胆的描写,成为唯一一部表现那个时代正常的人性、尊重女性身体和情感需求的一部“抗战”小说。小说中王柬之的妻子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女儿,被前者冷落多年,饥渴的性的本能驱使她将目光盯上了家中的长工王长锁:“她慢慢地注意到年轻力壮的长工王长锁。开始她是从窗口上、门缝中窥看他那赤臂露腿的黑红肌肉和厚实粗壮的体格……炽燃在女人心头的野性情火,使她愈来愈大胆地进攻了。”[102]终于,在一个风雪夜,她主动扑到了长工怀里。性超越了社会地位和阶级,并最终产生了爱情,而这爱情,对于二人而言,也是超越了伦理道德、阶级性甚至民族性的,小说中有大段描写表现这纯粹的超利害的爱:“他们为了保存私欲的爱情,王长锁可以出卖灵魂给汉奸当腿子,给王柬之到外村送信进行联 络……他自己深负内疚,受着良心的责备,可是他没有别的法子,只是昧着良心,为他的女人活着,为他孩子的母亲活着。杏莉母亲就本身的痛苦来说,她比王长锁更惨重。她不单是为王长锁当了汉奸,和他一道受着良心的责备、悔恨的煎熬;更加一层,她为了他又遭受过宫少尼的奸污……可是,她这都是为着保护他、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孩子啊!就这样把两个人完全缠在一起,为了保存共同的爱情不惜牺牲了一切。这种爱情关系已经和他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103]
这种所谓私欲的爱与前面正面主人公为国家民族的压抑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在此基于政治立场给予批判,而是基于生命本能的立场给予理解和同情,所以,在这一对爱情关系中,女主角的主动求爱既没有被描述为淫荡,也没有被男主角漠视或拒绝,而是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不是性爱为他者(民族/阶级)牺牲,而是他者为性爱让步牺牲,体现了人性的超越和解放,在“抗战”叙事的主流话语中,这样的描写相当离经叛道,所以,作者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为了使这种普通人的纯粹的爱有着更安全的表达形式,设置了两人最后觉悟牺牲在汉奸手里的情节,在牺牲前,两人还一起控诉了鬼子汉奸的罪恶并进行了反抗。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爱最终只能与民族主义话语相结合并以主人公的肉体牺牲为结束,但其如昙花一现绽放的生命力的火花也足以令人耳目一新了。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1965年的电影《苦菜花》中将小说中女性爱欲的成分彻底剥离出去,星梅的未婚夫铁功在电影中没有出现过,只是通过星梅跟“母亲”的对话提及,牺牲后出现在星梅回忆的镜头里,两人一实一虚,自然没有身体的接触。娟子和永泉也没有什么爱情戏,自然最后也不可能结婚。小说中的王柬之妻子、杏莉娘,在电影中不存在了。小说中的杏莉,既是母亲不伦情欲的产物,也是这段情欲的窥破者,在电影中改名为萍莉,并且改换了阶级成分,成为王家的仆人,穷人的孙女,从血统、阶级和道德层面都净化了。
新时期以来改编的“抗战”影视剧基本承袭了原著小说基于传统道德和乡土立场的审美标准,女性端庄自然的美是被肯定的。在男女两性关系上,女性依然是非理性的需要男性教导和指引的,比如2004年版的电视剧《苦菜花》中的娟子和永泉、星梅和德刚。比原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该剧把母亲也纳入这种情感关系的二元对立之中: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关于母亲的情感戏,而这个母亲,更加是非理性的受控于男性的,先是早年和王柬之有点暧昧的情感纠葛,继而为情蒙蔽,被清醒理智的姜永泉多次提醒仍不能觉悟。这样的一个改动仍然反映了当下影视剧基于商业利益的娱乐化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编的抗战剧与原著比变化比较大的是反面女性形象的塑造。其一,将阶级性与民族性分开,即地主阶级女性未必没有民族主义精神;其二,将阶级性与伦理性分开,即地主阶级女性未必是自甘堕落的、“淫荡”的。其三将民族性与伦理性分开,即失德的女性也未必失去民族立场。所以,在这些电视剧中,原著中的反面并且道德败坏的女性一变而为正派、有情有义,原著中的汉奸角色则变为日寇的受害者、民族大义的坚守者。比如前述小说《苦菜花》中的玉珍,在电视剧中,形象变得端庄清秀,对于生在地主王唯一家有原罪意识,认为是“落得一身脏”,和原著中主动跟多人鬼混的玉珍不同,她是被强奸的,并且很有贞洁意识。而且她还有革命意识和牺牲精神,主动要求加入妇救会,当娟子让她配合引出她的汉奸兄长时,她能大义灭亲,并且被挟为人质时,要求战士们别管自己,杀了其兄,最后壮烈牺牲。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王柬之的情妇淑花尽管在电视剧中还是一个反面人物,但也有变化,不再是一种刻板形象,从小说叙述中的胖的、淫荡的,变为镜头中的非常瘦的、清秀的女学生模样。
在不同文本中变化比较多元的是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的汉奸妻子二姑娘形象。在小说中她是一个风流放荡的形象,和汉奸刘魁胜打得火热。在1995年的同名电影中她名为小红云,由何赛飞扮演,不仅形象端庄,而且有道德和民族意识。当刘魁胜到她家里调戏她时,她表示嫁鸡随鸡,卖艺不卖身,不背叛自己的丈夫,后来她屈服于刘,也是因为后者捉了她的丈夫,她是为了救夫才不得已委身。最后,当日本人来请她唱戏时,她坚决拒绝,以自尽来成全民族大义。前面讲过,受20世纪90年代中日关系的影响,1995的电影《敌后武工队》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必然也影响到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对于族群来说,一个女人身体的贞洁和她的族群归属和/或者宗教的身份是同样重要的”[104],“维持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也是谱系民族主义者的关注点,婚姻与性行为(特别是妇女)的控制为民族的‘基因储备’的保证”[105]由此可以理解,在民族主义情绪比较浓重的抗战电影中,维护本民族女性身体的纯洁性和维护民族大义同等重要。电影《敌后武工队》先让小红云通过守节和救夫的行为变为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贤妻形象,同时赋予她一种传统地方曲艺技能——含灯大鼓,使其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符号,继而让她通过宁可自尽不为日本人卖身献艺的行为保持了身体的完整和纯洁,最终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符号。电影中的小红云为救夫可以委身于汉奸,对真爱自己的汉奸产生感情,但决不服侍日本人,也暗喻了上述谱系民族主义维系本民族血统纯洁性的意旨。1999年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的二姑娘基本依循了小说中的形象定位,但增设了一个原著小说中没有的人物——外号叫绣花鞋的女子,可以视为是与电影中小红云具有相同叙事功能的人物。此人虽然在乡里作风不正,但并非本性如此,而是在丈夫被鬼子杀害后为了谋生想改嫁,可宗法势力不允,为了让孩子活下去,只好偷东西,偷男人,也和汉奸马鸣有过偷情,但这样一个在乡人看来失德的女人却非常有民族大义,表示自己再不正派,还是个中国人,不会卖国当汉奸,最后在鬼子围攻乡人时拒不供出武工队情况而被敌人打死。这个形象就改变了前述小说中将民族性与伦理道德捆绑的倾向:即汉奸都是淫的,或者反过来说,有民族大义的人必然是谨守传统道德规范的,这种倾向只是反映了小说作者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立场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在世纪之交的电视剧中这种宗法伦理思想自然会淡化,但无论是小红云还是绣花鞋,不管如何和本民族男子有不正当关系,都能坚守住对抗异族的底线,还是反映了上述男性立场的谱系民族主义维护族群纯洁性的意旨。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在2005年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剧中的二姑娘一如电影中的小红云一样端庄正派,忠于丈夫,但相比小红云有着更为清醒的民族意识,后者只是最后拒绝为日本人服务而自尽,这里的二姑娘则时时提醒汉奸刘魁胜“日本人没有一个把中国人当人”,后来她还多次帮助武工队开展工作,最后向武工队透露了刘魁胜的信息,自己却死于乱枪之下。这里的二姑娘既具有小红云式的谱系民族主义的纯洁性,又具有前述符合民族国家话语的牺牲精神——牺牲爱情和自己的身体,所以她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小说中正面女性人物的某些特质。
综上所述,由红色经典“抗战”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尽管在阶级斗争色彩上较原著有所弱化,但民族主义话语甚至比原著还要强势,女性主义仍然是被压抑与服从的地位,包括将原著中富有母性的母亲改为“英雄母亲”,将原著中的反面女性一改而为端庄正派具有民族大义的形象,仍然是男性主导的民族国家话语的女性想象。
[1] 冯志:《写在前面》,载《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 冯志:《写在前面》,载《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 参见俞春玲《〈苦菜花〉及其他——冯德英访谈实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
[4] 参见俞春玲《〈苦菜花〉及其他——冯德英访谈实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
[5] 参见俞春玲《〈苦菜花〉及其他——冯德英访谈实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
[6] 参见金熙德《缔约30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日本学刊》2008年第6期。
[7] 参见金熙德《缔约30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日本学刊》2008年第6期。
[8] 参见李玉平《互文性 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4—75页。
[9]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10] 李玉平:《互文性 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11页。
[11]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2] [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李秉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13] [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李秉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14] [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李秉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15]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
[16]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17]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525页。
[18]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6页。
[19]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页。
[20]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5页。
[21]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
[22] 冯志:《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23] [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李秉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57页。
[24] [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李秉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25] [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李秉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26]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
[27]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76页。
[28]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122页。
[29] [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0] [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31]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32] 陈勤建:《民俗——日常情景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
[33]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34]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141页。
[35]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154页。
[36]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
[37]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
[38] 参见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选自王晓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93页。
[39] 熊锡元:《民族意识与祖国意识》,《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40] 参见吴密《“汉奸”考辩》,《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1] 陈兴中:《“汉奸”——中国历史、文化之痛》,《文史天地》2006年第7期。
[42]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04—305页。
[43] 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页。
[44] 参见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8页。
[45] 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46] 参见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页。
[47] 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页。
[48] 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6期。
[49]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页。
[50] 陈传海、石小生、郭晓平:《河南全民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51] 马甫平编著:《晋城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52]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44页。
[53] 冯志:《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54] 冯志:《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5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页。
[5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8页。
[57]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8页。
[58]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6页。
[59]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6页。
[60]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5页。
[61]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62]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63]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64]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65]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3页。
[66]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3页。
[67]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9页。
[68]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页。
[69]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页。
[70] 戴锦华:《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71] 转引自范若兰《暴力冲突中的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分析》,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72] 戴锦华:《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73] 陈传海、石小生、郭晓平:《河南全民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74] 参见[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李秉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75] [美]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选自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6页。
[76] 王微:《传统、革命与性别视域下的华北妇救会》,《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
[77]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页。
[78] 陈顺馨:《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79] [美]内尔·诺丁斯:《女性与恶》,路文彬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80] [美]内尔·诺丁斯:《女性与恶》,路文彬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81]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页。
[82]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页。
[83]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1页。
[84]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1页。
[85]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86] 参见王红欣《文化女性主义与简·亚当斯的社会思想》,《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87] [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不由己:关于性自主权的界限》,选自[美]伊丽莎白·韦德、何成洲主编《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9页。
[88]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7页。
[89]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
[90] 冯志:《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91] 冯志:《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92]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页。
[93]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94] 冯志:《敌后武工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95]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1页。
[96]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1页。
[97]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页。
[98]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页。
[99]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页。
[100]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7页。
[101]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7页。
[102]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8页。
[103] 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74页。
[104] [印度]布塔丽娅:《沉默的问题:分治、妇女与国家》,选自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105] 陈顺馨:《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选自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