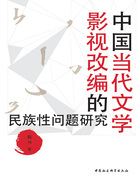
第二节 从文学到影视:民族国家意识的一脉相承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外来危机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及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在晚清时期由日本传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民族”与“国家”联结起来,形成初步的民族国家意识。“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中国’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鸦片战争的炮火迫使中国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瓜分,存亡危急,现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引进,社会政治运动,民族革命,等等,锻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使中国人凝结为一个民族的整体。”[11]在上层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民族主义是一整套理论建树,在下层百姓,则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
不论是红色经典“抗战”小说,还是后来以之为基础进行改编的抗战影视剧甚至“抗日神剧”,渗透其中的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不同时期都是一脉相承,贯穿始终,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顽强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在上述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家国思想、乡土情结以及“同仇敌忾”、抗击外侮的民族意识。
一家国思想。“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思想,“家”与“国”有着相同的治理模式和相同的血缘伦理基础,因而有着相同的情感认同,在这个统一体的差序格局中,较小的单位要服从较大的单位的利益,国家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成为一代代士人的自我道德追求,所以在中国历史叙事中多有为国尽忠的知识分子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家仇”+“国恨”的叙述模式就是叙述者“家国同构”思想的一个体现。在这些作品中,正面主人公的家庭都是破碎不全的,破碎的原因或是因为阶级压迫,或是因为异族侵略。所以正面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因为家族的血海深仇而有了血缘情感的基础,具有不易被撼动的坚定性,同时,中国传统的“还报”思想也使基于血族复仇的革命和抗争具有了伦理的正义性。小说和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正面人物的家庭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杨晓冬没有父亲,金银、银环没有母亲,韩燕来只有兄妹两人,周伯伯更是单身一人,金环的丈夫早死,只有一个孩子。小说《苦菜花》及影视剧《苦菜花》中,“母亲”的残缺不全的家庭结构是一样的,残缺的原因也都是来自地主王唯一家的迫害。小说《平原枪声》中马英的姐姐和父亲都死于苏金荣之手,所以他从小就经常表示“要给姐姐和爹报仇”。后来返乡后他把这种家仇跟国恨结合起来,针对家族的仇人同是也是勾结日本人的汉奸苏金荣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新世纪以后的电视剧则进一步强化了“家仇国恨”模式,“仇恨”的程度甚至远超原著,反映了时代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影视艺术追求戏剧性冲突的效果。比如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只是侧面交代了刘太生的母亲被日本人和汉奸杀害,魏强家则没有这样的家仇,而1999年版的同名电视剧则将主人公魏强的身世也设置了“血海深仇”:第一集开篇就是汉奸刘魁胜带着鬼子去魏强家抓了他的母亲和妻儿,其妻不堪受辱,跳井自杀,其子被鬼子枪杀。团长见了魏强,把其子的长命锁给他,对他说:这国恨和家仇我们一定要报,要让敌人加倍偿还。2005年版的同名电视剧将“家仇”范围进一步扩大,并突出了人物强烈的还报意识:刘太生的爷爷被日本人杀害,他马上不顾组织纪律去刺杀日本人,梁邦的弟弟和母亲死于日本人之手,他最后火烧敌人弹药库之前说的就是:家仇国仇一起报。
红色经典“抗战”小说和后来的影视剧在表现“家仇”的根源上有些区别,前者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并重,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中偏重阶级压迫,而新世纪的影视剧则淡化阶级对立,侧重表现民族压迫。比如《苦菜花》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母亲”一家和地主王唯一家的仇恨就有微妙的不同。原著小说中家仇的起因是娟子伯父的儿媳妇被王唯一的儿子王竹强奸,娟子家人复仇,然后又被地主迫害至家破人亡。这样的仇恨中固然有地主和贫民两个阶级的对立,但始于强奸的冲突其实更多伦理的色彩,淡化了阶级的对立。所以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中,两家的冲突变为纯粹的始于土地问题的阶级对立:娟子父亲因为被地主抢去一亩地,前去理论,被地主打伤致死,儿子德刚逃亡并表示“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要回来,回来给爹报仇。”电影中强化的是阶级仇恨,所以较少表现日军的侵略,到处死地主王柬之后影片就戛然而止。新世纪的电视剧中两家矛盾又渊于伦理冲突:“母亲”年轻时为反抗地主王唯一的淫威逃离王家,返乡后其女娟子又险些遭到王唯一的强暴。该剧中伦理冲突压倒了阶级对立,同时强化了民族对立情绪,反映了新世纪以后文艺作品淡化阶级斗争叙事、强化民族主义叙事的倾向。
“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的“家国同构”思想还表现在弘扬为民族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尽管中国传统士人有家国同构的思想,但对于习惯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农民来说,为了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家庭和个人利益还是一个相当的挑战。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伦理为纽带,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有固定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村落空间。抗战爆发前,中国大部分的村落都是这样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正如石岛纪之指出的:“太行地区许多村落的历史达千年以上……大体来讲,家族的观念很浓厚,血缘关系、宗族关系、辈分关系像网络一样盘根于这个社会。”[12]在这样封闭落后的宗法社会中,可想而知,近代以来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倡导的民族主义及20世纪20年代以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革命的影响都是非常微弱的,“1936年,北京周边地区农村还可见‘仍有农民认为现在还是大清朝’状况的存在”[13]。《吕梁英雄传》中康家寨的部分村民因为亲人被鬼子抓走,而被迫同意敌人的维持计划,就是基于血缘亲情的本能反应。然而,日军的入侵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改变了这一切。在石岛纪之看来,长期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破坏,然而也有“建设”和“变革”的一面,这就是“通过抵抗日本的侵略,也促进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想水平,尤其是它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及中国国家、民族的统一”。[14]在詹姆斯·贝特兰的书中也提到,中国人民正是从北方的山区里最早发起了抵抗侵略的战争,华北人民过去对谁来统治表面上保持着麻木不仁的态度,然而日本人的侵略和占领改变了这一切,“日本人残忍野蛮的行径,恰恰帮了八路军和八路军的政工人员的忙”[15]。在外敌入侵、灾难重重的乡土社会促进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思想水平,将他们从一盘散沙的状态凝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力量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利用民族国家的口号,对广大农村各阶层尤其是农民进行了艰苦的发动和动员工作,使原本松散的,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乡土社会的民众转而以国家民族为重,从血缘伦理亲情上升为民族大义、同胞之谊,从安土重迁转向离乡从军、奋勇杀寇。可以说,抗战时期是我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表现最集中最动人的时期,也是乡土社会家国观念、政治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
在红色经典“抗战”小说中,我们看到,党的宣传正是在毁于战争或阶级压迫的破碎的家的基础上,重新树立起一个完整的国族概念和全新的有关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党在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倡导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民族观念:“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16]“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17]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利益与国家民族休戚相关,现实的血的教训使农民比较容易接受有关民族主义的思想。小说《苦菜花》中,共产党员德松在群众大会上喊的口号就很切实地反映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想不当亡国奴,过太平日子,就得有人保卫祖国,不打走鬼子就别想安稳一天!有种的跟我来!参加八路军去!”[18]
在红色经典“抗战”小说中,普遍表现了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家国矛盾、艰难选择及最后的毁家纾难、取义成仁。《苦菜花》中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将对子女的爱先是扩展到并无血缘关系的同志,为他们做鞋、做衣服,“她爱每一个战士,爱整个八路军”[19],受尽敌人的磨难后,“母亲比过去更爱她所爱的人。这种爱早已超出爱子女爱姜永泉的范围,现在更扩大了……对革命同志,她从不吝啬自己的一切”[20]。母亲为了这种大爱将子女送入革命队伍,牺牲了长子,并为掩护军工厂又忍痛牺牲了幼女。《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主人公杨晓冬则是为了抗日工作牺牲了自己的母亲。在这里,宗法社会中母慈子孝的传统让位于民族大义了。小说中金环为了革命工作既能舍弃自己的丈夫,也能舍弃自己的幼子,她给儿子取名为“离”,这是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名字,暗喻为了国家民族的完整统一,个人要舍得“离开”自己的家。《苦菜花》中的农妇花子、党员娟子在敌人利用血缘亲情让村民认领自己亲人以识别八路军的时候,都没有认领自己的丈夫,而是认领了需要掩护的八路军战士,夫为妻纲的伦理关系升华为革命大爱了,正如小说中描写:“姜永泉只好接受她那不是妻子的,可比妻子伟大高尚的亲吻!一个老革命战士老共产党员,深切地感到,是人民,是母亲,在保护着他!”[21]更多的普通农民则是牺牲个人来成就民族大义,《敌后武工队》中的普通农妇快嘴二婶,接受了党关于国家民族的教育,宁死也不说出武工队员的下落,“死亡靠近了她,她并没有让死亡吓得想出卖良心。‘一个人为国家要宁折不弯,别做墙头草。’这是徐政委在公民誓约大会上讲的话;在庄严宣誓的时候,那‘不向敌人泄露秘密;不给敌人带路……’的条条誓词,都让她一下回想起来,‘我举手宣了誓,要说了不做,那算什么人?……’”。[22]《吕梁英雄传》中的农民张忠老汉为了掩护民兵引开敌人壮烈牺牲,比起乡绅二先生想要牺牲几个民兵换全村人性命的念头,境界高下立现,前者是民族大义,后者是宗法亲情。
以红色经典“抗战”小说为基础改编的影视剧与小说原著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家国观念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在后来一些旨在回归传统伦理的“抗战”剧中还有所强化。比如2010年版电视剧《平原枪声》中的建才和小说原著不同,表现出了很大的个体情感追求的自由度,鬼子用尽酷刑不能使他叛变,但他却为了自己的爱人安危而叛变了。剧中他被抗日队伍处决的下场就宣判了他的个人追求是错误的。正如马英对他教育:“没有大家,你和子芳的小家放哪儿?都和你一样,中国早就落小鬼子手里了。”
中共为农民提供的有关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是通过在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等土地政策落到实处的。这是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也是后来能广泛发动起务实甚至有小农意识的农民革命热情的关键要素。在前述石岛纪之的书中提到,“在农民的传统心态中,有‘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思想,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他们认为地主的土地是从祖先手中接过来的,对地主的土地下手是丧‘良心’。另外,还有寻求安定生活的‘太平观念’、等待世道变化的‘变天’思想,都在农民心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农民的这些传统心态,成为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社会改革的一大障碍”。[23]1939年到1942年,在各级党组织的细致调研和组织宣传的基础上,华北各根据地兴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让他们认识到是他们养活地主,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24]为了克服一般农村青年安土重迁、“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根据地实施抗日宣传、慰劳战士、优待抗属(士兵的家人)等政策。比如没收汉奸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抗属,组织代耕队帮助抗属耕种收获,减免抗属应承担的赋税,在各种庆祝会、纪念会上对抗属进行表彰,组织妇女制作慰劳品赠送士兵等”[25]。通过上述一系列政策实施和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仅使农村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而且极大提升了农民入党、参军的积极性,壮大、稳定了抗日的队伍。
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用了相当多篇幅形象且真实地反映了党在根据地实施的各项民生政策、开展的各项群众运动,有力解释了党在广大农村赢得民心取得抗战胜利及最终赢得政权的原因。《吕梁英雄传》开篇就介绍“新政权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使家家有活路,人人有饭吃,好发挥出一切力量齐心抗日,保卫家乡”。[26]书中还介绍为了稳定民兵的军心,春耕时民兵的地由变工队帮忙种;抗属康大婶平时经常得到抗日政府和村里群众的帮助、慰问,所以康大婶不断念叨:“抗属真光荣呀!给你叔捎上道信,把这事都告诉他。叫他安心打日本!”[27]《苦菜花》中记叙:“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合理负担的政策。并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土地,分给那些最贫苦的人们。当他们那长满茧的手,颤动地拿着新发的盖有民主政府的大红印的土地照时,两眼流出感激的眼泪,心是怎样地在跳啊!世道变了,是的,社会变了。但最使他们感动的是,能好坏使肚子饱一些,能说一句从祖辈不敢也不能说的话:‘啊!这块土地,是我们的!’”[28]这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在抗日政府新的土地政策实施后心态的变化。
基于国家民族思想的树立和保卫已有胜利成果的务实思想,小说中农民的参军热情高涨,几乎每部小说都有一个村民踊跃参加抗日武装的高潮场面。《苦菜花》中鬼子扫荡之后,在共产党员姜永泉的发动下,要参军的青年在“台子上排了长长溜”,王老太太赶着剩下的唯一一个健康儿子去报名,要他不要舍不得家。《吕梁英雄传》中康家寨村民在斗倒了汉奸劣绅分了粮食和土地后,为了防止敌人报复,共产党员老武发动大家参加民兵,马上得到了村里青年的热烈响应。《敌后武工队》结尾在处决了汉奸刘魁胜后,县委领导号召大家参军以取得最后的胜利,立即就有几百个青年报了名。这样的场面也是史料中记载的1945年根据地出现的空前的参军运动浪潮的反映。
在改编的“抗战”剧中有的涉及了根据地的民生政策,尽管所占篇幅不重,有的如2004年版电视剧《苦菜花》因为更侧重宅斗及情感纠葛等娱乐元素,对包括根据地民生政策和民主运动等方面史实几乎没有涉及。因此,与后来的影视剧相比,红色经典“抗战”小说全面真实反映了抗战时期华北农村的社会风貌及党在根据地的各项民生政策,更具有社会史意义,更能体现现实主义美学价值。
二乡土情结。日军的入侵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乡土社会所附着于上的土地被占领,而土地不仅是家和村落形成依附的基础,是乡村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关键要素,更是家国情结和民族意识附着其上的地理空间。“民族主义感情屡屡通过对过去的崇拜而表现出来,而这个过去,自然要体现在一块领土上。对于民族主义来说,领土就是承载民族过去的载体”[29],“世界上一切社会和文化都感到,扎根在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上才有安全感和认同保证。一切人类共同体都需要一块可以保证他们生活并通过它能表明自己存在的地理区域。”[30]所以,我们在红色经典“抗战”题材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叙述者用大量篇幅对当地风貌物产进行描写,表达出一种深厚的故土家园依恋情结和对家园被破坏的愤怒之情。比如《苦菜花》开头“楔子”部分对昆嵛山一带动人田园风情的描写,《吕梁英雄传》对吕梁山“土地肥美,出产丰富”的赞美,《敌后武工队》对“五一”扫荡前后冀中平原乡土风情的对比。上述这些作品的作者本身就出生于作品所反映的乡土社会中,所以这些充满诗意画意的田园风光的描写在实现政治使命和民族主义使命的同时其实还表达了作者本人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和赞美,比如冯德英就是在昆嵛山长大的,自称是“昆嵛山的儿子”,所以小说《苦菜花》的开头用大量篇幅介绍昆嵛山一年四季的美景及与“山”有关的方言俗语,尽管后面马上突兀地出现了关于贫富对立的描写,旨在引到政治主题上,但有关乡土风情的大量描写,比如“种种野花卉,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无论谁,都会把嘴张大,深深地向里呼吸,像痛饮甘露似的感到陶醉、清爽”[31],这样的文字其实是渗透着作者个人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并不能完全从政治与民族的视角去解读。
在改编的“抗战”影视剧中,依然具有乡土风光的镜头表现,但是个体的乡恋和审美体验逐渐隐退,从乡土扩展到领土,有关乡土的美好叙述就完全成为唤起保卫国土意识的起兴手法。所以电影中的乡土风光更多承载了表达民族主义思想或者阶级斗争意识的叙述功能。比如1995年版电影《敌后武工队》,作为影像文本,其乡土意识主要是通过主题曲表达出来的,在电影开头,鬼子突袭冀中平原的东王庄,伴着敌人残杀及村民反抗的场景,突然一个悲哀低沉的男声唱起了主题歌:“叫老乡,白洋淀上芦花香,是个好地方,春种秋收,有鱼又有粮,冬天暖来夏天凉,是个好地方;叫老乡,你快去战场上,快去把兵当,莫等鬼子来到咱家乡,老婆孩子遭了殃,快去把兵当;叫老乡,当兵要找武工队,多多打胜仗,平原山冈处处是战场,你我胜似天兵神将,多多打胜仗。”伴着关于白洋淀美好风光的歌曲,镜头中同时呈现的却是惨杀的场景,无论如何不会让人产生审美体验,唤起的其实是仇恨和歌曲后半部分想要表达的反抗及守土意识。而原著小说中并没有如上的文字,只是用了对比的手法描述了“五一”扫荡前冀中平原的风土人情,因为文字叙述的历时性关系,当读者读到美好风光的叙述时,还是会唤起审美体验的。1950年的电影《吕梁英雄》表现山西吕梁山一带风情是通过人物叙述、风光特写和歌曲表现出来的,也存在上述影片中将风光叙述与政治主题相结合的倾向,比如在影片开头,火车上一位解放军战士介绍“我和一排长的家在山西北部,那儿的地形很好,山连着山,水连着水,打起游击来挺方便的,共产党领着我们在那儿打了8年的仗……”这里的山西山水是作为党的游击战争的便利条件被叙述的。后面村民们在文艺晚会上所唱的地方小调,其歌词的叙述功能同上面《敌后武工队》的主题歌非常类似,也是先介绍地方景美物产丰饶,话锋一转,自从鬼子来了后,百姓遭殃,然后是共产党带领群众斗争,守卫乡土。这里的乡土风光既是作为对比,也是作为起兴,重点落在后面关于党的领导和抗战的正义上。值得提及的是,该电影的导演吕班本人就生长于山西,后来又在太行山一带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所以《吕梁英雄》这部电影也渗透了吕班本人对家乡山水的无关政治的热爱之情,比如在电影中不断闪回的山西的白云和山景,就给人以旷远之感,还有蓝天白云下相爱的青年男女哼唱的轻松欢快的山西小调,以及伴着村民们欢快热烈的麦收场面响起的同样充满热情的表达丰收及支援抗战的歌曲,扑面而来的田园乡土风情给受众以美的享受和热情的感染力。
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苦菜花》通过镜头语言能基本如实反映胶东昆嵛山自然风光,但因为该片主旨在表现阶级斗争,作为自然风光的土地就成了阶级压迫的工具,所以其中的乡土风光给人沉重压抑的感觉。比如电影一开头就是阴云密布、雷声阵阵的田野上,满脸愁云的农妇和小女儿在摘苦菜花的场景,继而一凄凉女声带着抖音唱起“苦菜花儿开满地儿黄,乌云当头遮太阳,鬼子汉奸似虎狼,受苦人何时得解放”,这一场景的叙述功能与上述电影相似,也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完全不似小说原著开头优美抒情的田园风光。2004年的电视剧《苦菜花》试图回归关于故乡田园的私人体验,所以开头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我的家在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的大山里,村名叫王官庄……母亲从小被卖到王家大院当使唤丫头”,然而随着这段话同时出现的却是青砖青瓦的深宅大院,让人马上联想到当时流行的宅斗戏,后面的剧情也表明,开头的乡土叙事是伪乡土,除了后面母亲返乡时出现了点荒山景象,后面的叙事基本在年代+情感+宅斗+谍战的框架内了,充满了流行元素,却失去了小说原著的乡土情结。
如果说田园风光属于物质层面的乡土社会,民风民俗则属于精神层面的乡土社会,所以在许多“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乡土情结通过民俗表达出来。“民俗,是民族或族群认知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精神生活形态,是民族共同精神生活中的‘我们感’,‘我们感’即人类族群或群体不约而同的感受,感性认知,心意趋同;它类同于文化认同,是文化身份的精神标杆。它由人们共同心愿的反复积淀而成。”[32]抗战时期,乡土社会的凝聚力依赖于文化认同,具有共同的情感心理基础的民俗就是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由此就可以理解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许多涉及了乡土社会的民俗,于激烈斗争情节的间隙,看似“闲笔”的风俗描写其实也表达了上述乡土家园之情,并作为民族主义叙事或阶级斗争叙事的重要情节推动力。
多部“抗战”题材小说及其影视改编作品对春节的风俗有较多的表现,这些年俗的描写在不同的作品中也有不同的叙事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表现上述的乡情。比如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多次提到杨晓冬的母亲希望他回家过年,为了实现让儿子回家过年的“理想”,“母亲很早便做了种种准备工作:她刨出水缸底下埋了六年的两块白洋,跑到很远的集镇上置买年货。腊月二十四她掸扫房屋,里外整得一干二净,二十六日蒸馒头,名义是蒸馒头,实则把发好的三斤白面,蒸了一对刺猬(用黑豆点眼),一双白兔(用赤豆点眼),一盘带红枣的花糕和许多莲花卷子。二十七日她蒸出了黏豆糕和猪血糕,二十八煮熟那挂加了葱花胡椒的血肠。这天夜里剁好肉馅,擦净灯盏,捻好灯花,灌满灯油,连煮饭用的柴火都挑拣了最整齐的”。[33]这样不嫌琐碎的细节描写一方面展示了北方乡村的年俗,一方面表达了民间对家人团圆的年的重视,同时,也为下文的“分离”作了铺垫。而这一家人的“分离”正是体现舍小家顾大家的民族主义精神的重要细节,所以后来年三十母亲见到儿子,想跟他说下自己为过年做的准备,暗地希望他回家团圆的时候,杨晓冬表示为难,因为自己还有工作任务,“我实在想跟你一块回去,跟妈妈一块过年够多好哇。不过我们进来很多日子,没做什么事,我们确实安排在今天夜里,狠狠地打击敌人一下。妈妈,我小的时候咱们说书唱戏不都说‘国破家何在’吗?答应你儿子‘先为其国,后为其家’吧!”[34]前面作为民间日常生活的年俗到这里就转变为民族主义叙事功能了,所以接下来的除夕就与传统意义的年俗有些背离,按照民间的传统,除夕之夜是有血缘亲情的家人的团聚,排斥异姓没血缘关系的人,然而杨晓冬的除夕是和韩燕来、银环等异姓同志一起过的,有写春联的民俗,但主要是在印制对敌宣传的传单。这样反传统的年俗也反映了作为现代革命的民族战争对宗法习俗的一种扬弃,所以接下来与工作着的杨晓冬们相对立的城市过年的热闹全都变成了负面事物:“除夕的夜晚,比平常热闹多了。大街上增加了路灯,到处播送着肉麻的黄色歌曲。商场里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男女摩肩擦背,奇装异服,到处泛滥着一种淫声妖气。唯利是图的老板们,不肯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他们临时张贴海报,甩卖各种应时商品。贪财的商店早已提前关门,麻将响得像摔惊堂木一样。市场外面街道上,不少缙绅大户,借着敬神的名义,实际上是逞威夸富,拿出很多鞭炮烟火,请了专门放花炮的,摆好桌凳唱对台戏。”[35]总体而言,小说中年俗的叙事内涵比较复杂,既有对民俗亲情的期盼和回归乡土的理想,又有国家危亡时不得已的舍弃和背离。1963年的同名电影还是能够一定程度地保留小说对民俗的重视,但或许因为篇幅受限,没有表现母亲对过年团聚的期盼和准备,所以围绕过年的纠结和舍弃就没有了,过年的场面只是几个镜头带过,而且这些镜头只是作为纯粹的年俗展示而存在,比如几个异姓同志在一起包饺子。电影中也有写春联的情节,但春联的内容更符合传统的年节气氛:“桃符万户更新,爆竹一声除岁。”而小说中写的春联内容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抒发了一种革命斗志,和传统的春联内容不太相合。总之,电影中的民俗是作为比较纯粹的乡土民风的反映而存在的,没有小说中关联家国取舍的复杂内涵。
小说《吕梁英雄传》第22回专门写吕梁山村康家寨过年的情节,在这一回里,写到旧历年关将至,尽管康家寨人经过敌人一年来的压榨,“家家都是想尽办法籴米买面,割肉打酒,忙着准备过年。到了除夕这天,雷石柱沿门串了一趟,见家家都在蒸馍馍,扫院子,贴对联,忙忙碌碌和日本人没来以前差不多”[36]。群众包括雷石柱都认为“一年三百六十天,就过的一个年,听说外国人是过阳历年,可是他们来到中国,也许要过一下老百姓这旧历年哩”[37]。所以村民们多数都不太担心了,雷石柱也按照当地过旧年的习俗,作起了准备:在除夕的当天垒好火塔子。张有义等人则叫嚷着初一一定要吃羊肉饺子。这里的村民们对过年的重视心理和年俗准备与下文鬼子大年夜的屠杀形成了冲突,其叙事功能则是通过反映敌人对年俗的破坏同时也是对宗法伦理的破坏来体现民族反抗的正义性,与孟悦分析的《白毛女》中黄世仁对年俗的破坏的叙事功能类似:冒犯了除夕这个节气,也就冒犯了这个风俗连带的整个年复一年传接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38]。同样,日本人冒犯了中国的除夕,在除夕夜突袭杀人,也就成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进一步成为民族的敌人。小说的民俗叙事由此就巧妙地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叙事了。2004年的电视连续剧基本是忠实原著的,所以如实保留了小说这一章回的情节。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传》及其影视改编作品中的春节在传统文化的视野里都是违和的,然后它们的民族主义叙事功能却是强大的,前者通过对传统的舍弃来弘扬了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通过叙述侵略者对民间传统的极端破坏来强化民族仇恨,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
三“同仇敌忾”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首先表现为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亦即认同;其次是在国家生活中,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兴衰荣辱、权利与得失、利害与安危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39]民族意识中包括对自身民族归属的认同,对本族利益的维护,同时也就包括对侵害本民族利益的异族的反抗精神。中国近代的“驱除鞑虏”口号和现代社会网民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言论都是民族意识的不同体现。民族危机时期往往民族意识凸显,人们的求同和排异心理都比较强烈,贯穿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的民族意识就是一种鲜明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民族忠诚感和对侵略者的仇视,前者的纯粹和激烈使得人们对汉奸这样一种民族背叛者的憎恶和仇恨程度甚至远超异族侵略者。
“汉奸”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出卖祖国利益的人”。该词源于何时,学界尚有争议,能达成共识的是,该词在清代已经广泛使用,与清中期及清末的边境冲突有密切关系,并在清末词义范围从汉人扩展为中华民族,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40]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汉奸”问题再次凸显,一是因为此时民族意识高涨,二是因为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形形色色出卖国家的行为,所谓“汉奸”数目众多,正如陈兴中所言“在入侵者的行列里,竟有超过百万人数的中国人在为日本侵略者奴役自己的同胞服务。这些就是被人所鄙弃的‘汉奸’。世界上任何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总避免不了一些个人或群体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成为侵略者的帮凶。但是像中国这样存在着如此庞大的叛国者的队伍,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却是极为罕见的”[41]。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堪称第一人反派的通常不是日本鬼子,而是各类汉奸形象,他们往往冲在鬼子残杀国人的前线,对同胞比鬼子还要凶残,所以也成为抗日民众的主要敌人,是小说或影视剧中矛盾冲突的主要对立一方,在很多小说或改编的影视剧中,大部分情节都围绕展现汉奸之恶及对汉奸的斗争展开,篇幅远大于表现与鬼子斗争的情节。这样的叙述轻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与汉奸斗争的史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一种民族情绪。小说《苦菜花》中在公审王唯一时有段反映群众心理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上述仇视汉奸甚于鬼子的民族情绪:“人们都很激动,怒视着这群东洋的奴才。淳朴的人们,往往仇恨汉奸更甚于日本鬼子。他们的想法是:日本鬼子生来就是坏的,就和狼一定要吃人的道理一样;可是这些同国土同民族的败类,却出卖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做敌人的帮凶;他们就像是失去人性变成豺狼的人,比野兽更加可恶。”[42]
为了表达对汉奸的仇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除了渲染铺陈汉奸之甚于日寇的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害,还将伦理道德与民族性问题捆绑在一起,形成正相关的关系,即凡背叛本民族利益的也必违反传统伦理价值观,道德水准低下。所以,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汉奸普遍道德败坏,人格低下,不仅同族的人仇视唾弃他们,即便日本人也瞧不起他们。
在“抗战”题材小说中,汉奸的道德败坏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男女关系混乱,或者说传统伦理中作为万恶之首的“淫”。小说《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中都有对汉奸荒淫行为的描述,到了1999年版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汉奸将自家众女眷都献给鬼子淫乐,反伦常行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这种汉奸之间“共妻”然后献妻与侵略者的情节在多部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中都出现过,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叙述。比如小说《平原枪声》中汉奸王百顺先是把老婆“红牡丹”献给苏金荣,之后又“转租到王金兰名下”,日本人来了后,又献给了鬼子中村。
2000年以后改编的影视剧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上有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汉奸仍是反面的丑类的群像,但影视剧开始表现人物内心的复杂和挣扎,使得反面人物在男女婚姻关系中的行为具有了人性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比如2010年版电视剧《平原枪声》中杨百顺的妻子“红牡丹”尽管也与苏金荣和日本人私通,但与小说中心甘情愿的奉献不同的是,剧中的杨百顺是迫于对方压力而不得已为之的,所以他的内心对霸占其妻的苏金荣和日本人暗暗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他暗杀了苏金荣。同样,2005年版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的汉奸“哈巴狗”对于其妻二姑娘和汉奸刘魁胜的私通起初并不知情,知道了以后表现得非常痛苦,甚至准备去找刘魁胜拼命。和原著差别更大的是,剧中的刘魁胜对二姑娘不仅仅是欲的念想,而且有了情感的因素掺杂,所以他打算娶她。总体而言,改编后的影视剧中的汉奸虽然婚姻男女关系和小说一样仍是混乱的、不洁的,但不再是只有本能冲动,而是有了情感的因素,表现出了宗法伦理的影响。实际上,传统的宗法伦理对于家族血缘的纯洁性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出身于乡土社会的汉奸不可能不受这一宗法伦理的影响,小说中描述的汉奸们主动情愿的献妻行为的真实性确实令人生疑,应该是叙述者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一种叙述策略,其叙述功能类似于上述《白毛女》中黄世仁的反伦理行为。
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汉奸之丑恶还表现在对待同胞比日本侵略者还要凶残,在这些作品中,每次为日军屠杀打前阵的都是汉奸,为日本人出谋划策对付同胞的也是汉奸。所以,从这一角度说,汉奸的负面效应要远远大于日本侵略者。如果说,在小说中汉奸和侵略者的负面形象还相差不远的话,到了当代影视剧中,则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在一些电视剧中,甚至出现了从人性和道德上美化侵略者,而竭力贬低和丑化汉奸的问题,比如前者往往显得有文化,有涵养,甚至有血性,而后者则下贱无骨气,对前者卑躬屈膝。比如在1999年版的《敌后武工队》中,鬼子一撮毛练习刀法,胖子苟润田(伪警察所长)不仅形象不佳,而且丑态百出,极尽谄媚之能事。尽管在小说中苟润田也是被丑化的形象,但并没有这么夸张的情节。2005年版《敌后武工队》中汉奸刘魁胜在跟日寇要拨款时表情动作极尽奴颜婢膝,而日寇坂本则严肃深沉,一幅高高在上的样子。当前者向他告密的时候,坂本却说其实瞧不起他这样的汉奸,这样的表述未必是历史真实的情境,倒更像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情感表达。2000年以后一些具有早期“神剧”色彩的电视剧在表现汉奸低俗的同时,把侵略者表现得有品位,有修养,甚至还重感情,或许是想改变过去文艺作品中关于鬼子的刻板形象,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明显背离史实,比如2010年版《平原枪声》中,日寇中村显得很有中国文化修养,不仅大谈茶道,出征前还念中国古诗,同时又兼具武士道精神和骑士精神,人格显得比汉奸高尚并且还尊重女性。所以,无论是过度表现汉奸的反伦常行为,还是后期“神剧”中将日寇表现得有文化涵养,有人格理想,都不是抗战历史的真实反映,都带有了艺术夸张色彩,前者是民族情绪、民族意识的投射使然,后者则是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大约在2000年以后,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热潮下,诸多抗日题材的影视剧都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和臣服,来表达一种文化抵抗和民族自信。比如上述电视剧《平原枪声》和2005年的电视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都有一个醉心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师的日本侵略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