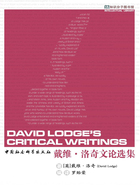
前言
在西方文学中,戴维·洛奇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正如他的小说在国内外拥有大批读者一样,他的文论在中外学界也广为人知。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译介戴维·洛奇文论的著作,希望有助于对洛奇文论进行更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更好理解。
本书的选编原则是力图展现戴维·洛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如下几个方面:洛奇文论的发展演变过程(文章编排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及各个阶段(新批评、结构主义、巴赫金理论、新世纪)的理论精华;洛奇所倡导的和探索的诸种文学理论以及他的批评实践对这些理论的应用;洛奇对英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及其各流派的经典分析。
具体来说,本书选入的文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小说诗学探索,包括“小说的语言”、小说话语类型学、小说与意识的关系、传记小说的特征等;二、小说发展史的梳理和研究;三、现代文学,特别是英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梳理和研究;四、小说创作实践研究,包括作家与读者及其接受的关系、作家及其创作与出版和文学市场的关系研究;五、小说与其他媒介的关系研究;等等。
本书所选文章的内容偶有重合,但论述角度和详略各不相同。
在此,编者将对全书内容做一个基本上属于描述性的概述,粗线条地、但力图完整地勾勒洛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呈现他在各时期的理论要点,交代其背景,体现其演变的逻辑和整体性。
戴维·洛奇一直致力于小说诗学的探索和建构。《小说的语言》一书就是他最初的尝试。此书主要写作于1963—1964年。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小说批评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的观点,强调“小说家的媒介是语言,无论他做什么,作为小说家,他都是使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做”。[1]此书出版后一些重要评论家和包括《卫报》、《每日电讯报》在内的著名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进行评介。洛奇在2002年为此书再版所写的“前言”中写道,一个年轻人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受到如此关注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其原因除了他当时已是三部小说的作者而小有名气外,主要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批评作者还有可能写作同时为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所理解的著作,而且那时书市上此类著作尚未出现过剩。他暗示,这本书跟自己的创作经验无关,他于1986年从大学退休后,才开始将文学批评与对自己“写作实践”的反思结合起来。[2]
在确定本书篇目时,编者原本打算将洛奇较为全面阐述《小说的语言》观点的《走向小说诗学:一种语言研究方法》(Towards a Poetics of Fiction:An Approach through Language)[3]一文编入本书,以便读者对《小说的语言》一书的内容有一个概要性的、感性的了解。但尊重洛奇教授的意见而放弃了那篇文章。不过洛奇1984年为《小说的语言》第二版所写并收入本书的“后记”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在《〈小说的语言〉第二版“后记”》中洛奇写道,对于写于二十多年前的《小说的语言》的第二部分,除了有关哈代创作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部分,他不想收回任何观点也不会做任何重大修改。第二部分都是关于单个文本或者作家的评论文章,它们通过“相似模式”、“平行结构”、“重复”和“对称性对立”等所谓“空间形式”对小说的“整体意义”进行解读,并试图表明,这种形式批评的范式也适用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
洛奇对《小说的语言》一书的保留意见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的理论阐述。现在,洛奇不再坚持“新批评关于抒情诗的所有论断都适用于小说”、“小说批评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作家控制小说人物和情节发展变化的一些“决定”和“抉择”与文本的“表层结构”不可分割等观点,因为他认识到,建立在抒情诗基础上的诗学不能简单移植到叙事文学上来。当初提出所谓的“不可分割论”并付诸批评实践的原因,在于当时新批评作为一种成功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其应用并不涵盖小说;另一方面,主导小说批评的则是主题式和道德化批评话语,并不涉及小说的“叙事元素”。
直到后来,洛奇才发现一种真正可以将文本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综合起来、将英美新批评与欧陆结构主义结合起来的小说诗学。
戴维·洛奇“十字路口的小说家”这一著名说法源于20世纪60年代小说创作在模式和题材方面惊人的多样性。洛奇说当时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所以《十字路口的小说家》这本书的书名实际上应为“十字路口的批评家”。该书集结的批评文章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是变化多端。自己的批评实践使洛奇开始意识到,《小说的语言》一书限制了文学批评的目的和方法的多元化,而这恰好是他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书中定义并为之辩护的。虽然他仍然使用语言研究方法,但他承认,极力为《小说的语言》进行辩护的《走向小说诗学:一种语言研究方法》一文中“所有好的批评都是对语言的反应”的观点放在这本书中也许令人“费解”。[4]
洛奇认为,文学批评的多元化跟学术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报刊的相互渗透、贯通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正是当时文坛的显著特征。[5]
与本书同名的论文《十字路口的小说家》无疑是该书在文学观点、方法方面都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文中,通过评论《叙事的本质》和《寓言编撰者》两部著作,洛奇从类型学上对小说发展进行梳理,并探讨“小说向何处去”的问题。洛奇认为,从文学发展史来看,现实主义小说是容纳历史、罗曼司和寓言等因素而形成的综合体;当今小说家(主要是英国小说家)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他站在一条向前伸展的传统现实主义之路,即虚构模式和经验模式的妥协之地,十字路口伸出两条方向相反的岔道,一条通往“非虚构小说”,另一条通往“寓言编纂”。小说家在十字路口的犹豫使第四种小说,也就是所谓的“问题小说”出现,它将小说创作所提出的美学和哲学问题本身写进小说,让读者分享这些问题。洛奇强调,我们似乎身处史无前例的文化多元时期,各种艺术的多样形式同时蓬勃发展,没有一种成功占据主导地位,批评家必须避免拿适用于一种形式的标准去评判另一种形式。该文的结论是对现实主义小说未来信心的适度肯定。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实主义?文学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构成当代文学形式和风格变化的基础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个综合性文学话语类型学,它可以描述和区分所有文本类型(包括现实主义小说),避免未审先判。这是洛奇在《现代写作模式》一书中所探讨的问题。
接触雅各布森理论之前洛奇注意到,在使用比喻修辞方面,一批反现代主义作家(奥威尔、格林等)偏爱使用明喻而不是隐喻,而另一批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伍尔夫等)则刚好相反,他们大量使用隐喻。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所发现的这一区别很快融入了一种更为强大的理论,即雅各布森的隐喻/转喻区分理论。原来,为了为布拉德伯里主编的《现代主义》(1974年出版)一书撰稿,他循着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们对雅氏的引用,查阅了雅氏《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个类型》一文,他将阅读那篇文章的经历描绘为“受到雷击般的震撼,顿如醍醐灌顶”。[6]他发现,隐喻/转喻区分理论不仅仅是一个远比隐喻/明喻区分更为有效的用于区别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小说语言的方式,它还提供了建立一种适用于一切写作模式的文学话语类型学。雅氏关于现实主义小说转喻特征的简短评论,使洛奇特别为其显而易见的强大解释力而兴奋。雅氏理论还为他提供了打开一些紧闭的结构主义理论之门的钥匙。
洛奇说他自己一直是个形式主义批评家,醉心于小说研究的部分原因是小说这种文体对形式主义批评的抗拒所带来的挑战。如上所述,他写作《小说的语言》一书时认为,“小说批评的所有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语言问题”。他认为这一论断在理论上无可辩驳,但它导致方法论上的困难和缺陷,导致语言或者文体跟情节、人物等范畴形成对立。而隐喻和转喻这一对对立概念是形式主义理论的结构主义变体,它有资格化为一个更具涵盖力的文学形式理论。“从单个短语或句子,到情节结构或者情节类型,一切都是形式”;“在最小的和最大的结构单位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为一切都卷入同一个基本的选择与组合、替代和删除过程。”隐喻/转喻区分理论“揭示的不是内容,而是符号的系统性结构,内容在这一结构中得到理解”。[7]
本书选入了反映《现代写作模式》一书基本理论思路和观点的《什么是文学》一文,分析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各种写作模式此消彼长格局的《两类现代小说》一文,以及洛奇系统阐述雅各布森隐喻/转喻区分理论,并对其进行完善和发挥的《隐喻和转喻》一文。
《什么是文学?》一文分析了形成二元对立的两类文学定义,提出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话语类型学,借此既能区分文学话语和非文学话语,也能克服文学理论中模仿论和审美论两种派别厚此薄彼、水火不容的倾向,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类型学将使传统批评所忽略的散文小说进入诗学的范畴。洛奇认为,捷克结构主义的“前景化”理论有望为一种“综合”理论提供基础。该文援引穆卡洛夫斯基的“扭曲”说和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结合韩茹凯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托多洛夫、费什、卡勒、威窦森等人的有关论述,力图形成一个可以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的“综合”理论。文中批评了对阅读角色的片面抬高,强调写作与阅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两类现代小说》中,洛奇以著名的“钟摆”理论勾勒出英国20世纪上半叶文学(特别是小说)发展的轨迹。在20世纪头十年,崭露头角的现代主义运动受到压制,现实主义引领文坛;10年代,部分现实主义作家向象征主义发展;20年代现代主义名家、名作辈出;30年代在形式上回归纪实性现实描述标准,挑战现代主义;战后英国小说也可以被称为反实验时期,现代主义在40年代出现复兴。洛奇对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小说家们进行了归类。他指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摆钟运动已经加速。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何谓现实”之争中,与其争得你死我活,不如接受两种现代小说持续共存的局面。为此,他指出,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描述所有写作类型的小说诗学。
《隐喻和转喻》(《现代写作模式》第二部)就是洛奇试图建立上述小说诗学的新尝试。洛奇说,这里与其说是雅各布森理论的概述,不如说是对它所做的理论性拓展。[8]洛奇认为,雅各布森在隐喻和转喻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中,对转喻可谓轻描淡写甚至忽略,而他提出可以用转喻的“删除”对应选择的替代,以填补雅氏留下的空白;传统上人们将隐喻和转喻看成同一类修辞,洛奇指出,根据本体和喻体之间是否存在相邻性可以确定隐喻和转喻之间的界限或者对立性质;雅各布森创造性地应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失语症的两种类型,为其隐喻/转喻区分理论提供了依据,而洛奇则似乎在对失语症的病理分析中找到了打开现代主义文学“晦涩”之门的钥匙;针对文学理论严重地偏向韵文文学而不是散文文学,为了维持其二元结构的平衡,洛奇提出以“相邻性原则从组合轴向选择轴的投射”这一命题对应“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向组合轴的投射”,以描述诗性功能的转喻性方面;该文还分析了为什么诗学里缺乏对转喻模式的论述,转喻模式何以成为“诗性的”,为什么要重视转喻模式的写作等问题;洛奇还提出,可以以隐喻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来确定文本的文学性和文体类属。以隐喻/转喻区分为理论模式,洛奇用5个描写城市的文本片段,比较分析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差异,并将5篇表现死囚的小说从转喻极到隐喻极进行排列,形成一个话语光谱图,逐一分析其隐喻性和转喻性。
洛奇坦言,没有人可以否认六七十年代欧洲结构主义对文学和文学批评产生的深刻影响。对它进行抵制是徒劳的。洛奇对结构主义的态度在下面将要讨论的这本书的书名上就得到了反映:《结构主义的运用》(Work with Structuralism)。“working with”包含的意思不仅是指将某物作为有用的工具来运用,还指“与它共事”(working alongside it)”,也就是说,认可其存在但不受其支配。洛奇说其实本书还可以命名为Living with Structuralism,意为“忍受结构主义”。[9]由此看来,汉译书名“结构主义的运用”是不准确的或者不全面的,但此译名似乎已约定俗成。现有译名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结构主义强势影响的认同(在“运用”/“应用”和“共事”两个义项中选择前者),也可以说,它反映了翻译表达的局限性。
结构主义席卷学术界的结果是学术界的多重分裂,学院内部是教学与研究的分裂,学院外是学术批评语言和普通评论与文学刊物语言的断裂,作家和文学记者像18世纪那样对学术批评又怕又恨,同仇敌忾。而积极卷入以上四项活动(大学教学、学术批评、为文学刊物撰稿、写小说)的洛奇,力图维护四种话语之间的联系和连续性。
《结构主义的运用》所收文章作于70年代,它反映了洛奇所亲身经历的结构主义的影响。部分文章虽然吸收了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没有由此变得对除极少数专家之外的大多数人晦涩难懂。洛奇将结构主义分为“经典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认为后结构主义的故弄玄虚和吓唬读者的行径经典结构主义只是偶尔为之,而本书文章“运用”的几乎只是经典结构主义批评话语。洛奇的兴趣就是运用结构主义的概念与方法为文学批评添砖加瓦。[10]该书的主体部分是“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对经典现实主义小说进行形式主义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洛奇在哈代小说精心设计、独具一格的结构中,居然发现雅各布森“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向组合轴的投射”这一美学原则被运用到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能容许的极致。[11]
《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文的重要部分是应用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欧洲结构主义文论的若干概念,从文学内部,也就是从形式上寻找百年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并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定义英国现代文学中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类型:现代主义主要是隐喻模式,反现代主义主要是转喻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挑衅这两种模式并找到了新的写作原则:矛盾、并置、中断、随意性、过分和短路等。“陌生化”使我们在社会历史动因之外找到了文学演变之美学上的和形式上的动因,隐喻/转喻区分理论则解释了英国文学为何往复循环(即呈现所谓“钟摆运动”),并总是重复上一种风格之前的风格。
《化不幸为金钱》一文跟结构主义并没有关系。它收入《结构主义的运用》一书,如洛奇所言,反映了他为之辩护的批评话语的多元主义。此文也代表了洛奇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探讨。老牌的文化产业和软实力强国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出版业危机(特别是小说出版危机)和洛奇对它所做的分析,可资借鉴。洛奇认为,小说的命运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70年代的出版危机就是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小说家来说,写小说是一项高度个人化且竞争激烈的活动,作品在市场上的命运是评判其创作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政府的干预作用有限。英国的文学市场仍然发挥着大浪淘沙、择优汰劣的功能,但目前(70年代)的危机如果持续下去,也许会走向炒作为王、成本高企的文学市场之美国模式。
《盎格鲁—美国姿态(1965):英美小说中的范式》一文选自洛奇评论集《写下去》。跟洛奇此前甚至之后发表的批评著作相比,《写下去》一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明显没有统一的主题或理论方法,都是受约而作或因“要写点什么”的冲动而作,二是据洛奇本人说,该书文章是写给范围更广的读者而不只是专业学者看的。[12]不过《盎格鲁—美国姿态(1965):英美小说中的范式》一文选入本书出于编者专业上的兴趣。该文认为,美国小说缺少英国小说的坚实、均衡和完整,但是它更为大胆,而且更为深入地触及人类境况。美国文学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把美国方言土语作为文学的活力源泉。而英国小说家创造并保持着他们独特的作者声音,这种声音将形式和对自身经验的感觉融为一体,并说服读者接受它们的合法性。美国作家脱离传统文学范式标准的相对自由,既导致其缺陷也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文学召唤一种新的范式,一种非范式的范式。
《盎格鲁—美国姿态(1965):英美小说中的范式》一文对英美当代小说各有褒贬,但洛奇20年后在为再版《写下去》一书写的“前言”中表示,让1986年的他再来比较当代英国和美国小说,他就不会对后者那么恭敬了。[13]
洛奇在《巴赫金之后》一书的前言中,回顾了他与巴赫金理论结缘的过程,以及巴赫金理论对当代文学批评和创作,乃至当代哲学思潮的意义。他认为,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属于结构主义,70年代属于解构主义和其他后结构主义,那么80年代就是巴赫金著作的发现和传播时代。巴赫金的理论给那些开始怀疑解构主义之后批评理论是否已死的文学批评家以新的希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来说,它复活了语言和文学的社会建构功能的概念;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它复活了一种历时的、基于语言学的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他又为分析和归纳叙事话语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对洛奇本人来讲,巴赫金的理论使他认识到他在《现代写作模式》中仍没有完全摆脱大多数文体批评将小说语言当成一个纯一实体的倾向,认识到小说是多种文体、语言,或者声音的混合体。巴赫金的理论还解释了洛奇为何是小说家而不是诗人,为何醉心于拼贴和滑稽模仿。最后,他指出,巴赫金对当代文学批评做出的最伟大贡献,是他及时重新肯定了作者创造和交流的权利,而这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进行诋毁并试图以“文本自动生产”和读者理论取而代之的概念。
洛奇说“巴赫金之后”有一丝“挽歌”的味道,因为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当代学术性文学批评背离了批评的初衷,而他此后也将不再写作他所说的学术性批评文章。
收入《巴赫金之后》一书的文章,大都是巴赫金话语类型学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在《当今小说——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洛奇指出,在传统人文主义关系模式下,小说与批评之间有着积极的互动和影响;但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正如他在《结构主义的运用》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后结构主义的流行导致批评与小说创作及其接受的分离。后结构主义颠覆作者的概念和小说与现实关系的概念,作为小说家的洛奇对这两点都提出异议。不过小说家的确面临与生俱来的事实与虚构的矛盾,这是现实主义小说中隐含的问题,而元小说让它走上前台并得到彰显。巴赫金的小说理论超越人文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对立,为小说的存在进行辩护。洛奇认为,英国当代文学,包括劳伦斯、伯吉斯、托马斯等人和洛奇本人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杂语性、狂欢化等一系列复调小说特征。
洛奇认为,现代小说话语复杂而精妙,柏拉图的模仿/叙述区分理论不足以曲尽其妙,将它与巴赫金的话语理论结合起来,便可以形成一个完善的分类系统。《现代小说的模仿与叙述》运用这一分类系统对以《尤利西斯》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的话语模式和英国小说演变的历程进行了分析。对这个话语分类系统来说,《尤利西斯》就像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文本,它包含了叙述、模仿以及将二者融为一体的自由间接风格,还有包括仿格体、滑稽模仿、口述体、暗辩体在内的所有“双向话语”。洛奇指出,18世纪英国小说保持了模仿和叙述之间的平衡;19世纪的经典小说沿袭这一模式,但间接引语的使用打破了叙述和模仿之间的清晰界限;现代主义小说模仿多于叙述;后现代主义在形式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对叙述的重视,叙述者将叙述活动中的有关难题和写作过程写进小说,在那里,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变成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流。
如果说《现代小说的模仿与叙述》一文重点分析了比较典型的“复调”式文本《尤利西斯》,洛奇在《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一文中则尝试以被认为跟“复调”看似没有相似之处的D.H.劳伦斯的创作来验证巴赫金理论的适用性。一般认为,D.H.劳伦斯的小说风格单一,观点统一,但洛奇认为,他的某些作品以及一些作品的某些方面,都包含巴赫金所定义的复调小说的特征。洛奇指出,劳伦斯的创作与巴赫金理论的契合不仅限于形式,在社会政治涵义和哲学观点上都存在有趣的相似之处。
洛奇在《现代小说中的对话》一文中进一步扩大他运用巴赫金理论研究现代小说的范围,认为沃作品中的反讽,拉德纳、亨利·格林和伯内特的标点使用以及状语修饰语的使用,都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双声语”。他指出,许多经典小说(包括现实主义小说)中都存在语言多样性,任何一种文学话语都含有暗辩体。
巴赫金理论留下了一个哲学难题。洛奇在《巴赫金之后》一文(该文与《巴赫金之后》一书同名)中指出:“既然对话是语言的固有本质,为什么还会有独白话语?”洛奇尝试对此进行分析和解释。他认为,也许在书面语里由于语言接收者缺席于语言行为语境,致使写作者忽略或者压制语言的对话维度,就此产生独白话语的假象。巴赫金曾以“小说化”这一概念描绘文学发展过程中小说文体对诗歌文体的渗透,就此模糊对话文体和独白文体的界限。洛奇认为,可以在主导性和“倾向性”的意义上应用对话/独白的区分,将它们看成两种互不排斥的类型,即根据文本是利用和称颂生活言语固有的对话本质,还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文学效果而压抑和限制它,来发展一种写作体裁或者模式的类型学。
1987年是洛奇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此辞去教职,成为全职作家。此后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从各个方面聚焦写作实践,纯理论研究较少。1996年出版的《写作实践》一书便体现了这一转变。洛奇说他“最喜爱写作和阅读这样一类文学批评,即探讨文学和戏剧作品如何创作,描绘创作过程中产生作用但并不总是处于作者控制之下的许多不同要素。”[14]《写作实践》一书诞生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当时英国高校文学创作课程(Creative Writing courses)的兴起,它有取代19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传统理论课之势,该书为教学文学、创作和媒体的师生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也算应运而生。
《今日小说家:仍在十字路口吗?》是20年前写的《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文的姊妹篇,从题目来看,它研究的问题跟前篇一样,但从其内容则可以看出,洛奇的文学批评写作风格和关注点已经大不相同。洛奇认为,二十年后,《十字路口的小说家》所呼吁的美学多元主义已是文学生活中被普遍接受的事实。现实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寓言编纂依然兴旺,非虚构小说主要在美国流行,问题小说或者元小说也继续发展。《十字路口的小说家》分析的是不同作品的不同模式,而今天小说创作的突出特征是“交叉”,即在一部小说中,上述一种或者多种文类与现实主义混合,形成所谓“交叉小说”。不过,大批最有声望的小说家仍然完全使用传统现实主义的话语方式进行创作。二十年后,文学生产面临的新形势是,文艺小说(literary novel)在八十年代获得了商业上的价值,但九十年代的经济衰退使出版业经济和小说家的生计难以为继。社会经济状况、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对作品的形式和作家对读者的态度,以及作家对商业活动的参与等都产生着影响。这种强大的影响力被普遍认为有着文化上的破坏性。
《作为交流方式的小说》是洛奇在剑桥大学做的一篇命题演讲。论述小说作为交流方式的特征,他一如既往地批判解构主义对作者地位的消解,捍卫作者在文学中的交流地位。洛奇指出,传统小说家将自己视为致力于跟读者交流的对话者,而现代主义小说家常常在作品中传达交流困难或者交流根本不可能的信息。在巴赫金看来,语言本质上是对话性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表述都直接指向某个要接受它的他者:作者就是通过创作跟过去和未来的“他者”交流。
《小说、影视剧、舞台剧:讲故事的三种形式》包含洛奇对跨媒介写作的理论探讨和亲身实践经验的分析。本文旨在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三种叙事形式的独特性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使艺术家倾向于一种叙事形式而不是另一种,什么促使作家转行尝试另一种叙事形式,转行后他们对叙事的本质有什么发现。他指出,小说家的交流媒介几乎只有语言,在小说出版并接受读者评鉴之前,小说家可以保持对文本的绝对控制;因为戏剧和影视的多媒介协作性质,剧作家不可能不根据合作方意见对自己的剧本做任何修改,但合作中的某些冲突和争论可以形成创造性的艺术张力。小说家用来将素材变成艺术的一些手段,戏剧或电影中几乎是不可用的;反之亦然;小说使用较多冗余以强化对人物的理解,并让阅读变得轻松,而电影中的冗余主要是影像,电影对白的冗余越少越好。从事剧本创作有苦有乐,演员的表演可以让你意想不到地挖掘出你写的台词的潜在表现力,你的作品有了以多种不同渠道进行共时交流的可能性。
洛奇继续为非专业读者写作非纯理论性批评文章,但发表于2002年,并与洛奇的新评论集同名的文章《意识与小说》算是个例外,虽然这里的“理论性”并非后结构主义式的。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洛奇发现意识成为科学的热门话题,而且科学关于意识的结论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关于自我和人性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发现使他萌生了创作小说《想……》的想法。为此他研究了大量有关理论文献,这些研究又促使他对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进行了反思。这些研究和反思就形成了这篇十分“理论化”和“专业化”的文章。洛奇认为,在意识受到科学和人文双重关注的情况下,把握意识的最佳方式是科学和小说结合。因为意识是个体化的、第一人称的、复杂的,而科学是追求规律和公理的,是第三人称的,简约化的;只有小说既是个体化的,也可以是第一人称的,可以以其修辞和技巧表现意识的复杂性。小说观念的基础是人文主义的自我和个体概念,而自我和个体,以及随之出现的身份认同问题都和意识紧密相连。人的意识所具备的叙事特征决定了小说与意识的天然关系。小说的自由间接手法融合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种叙事形式契合科学与小说结合的诉求。似乎在洛奇看来,意识与小说的关系是本质性的。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关系的难题也跟意识有关。洛奇在《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文中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分为四类:补充型、对立型、创造型、包含型。批评的难题是文学批评试图理解文学创作的本质,而文学创作是意识活动,意识活动的“多重草稿”模式决定了其变动不居、难以把握的性质。
洛奇后期的文学批评如他所言,都聚焦于作家的创作实践,从《写作实践》一书开始,到《意识与小说》、《亨利·詹姆斯年,小说的故事》(2006)和《写作人生》(2014),[15]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小说家写作经历的研究以及从创作实践角度对他们的作品所做的分析,部分文章谈的是他自己的创作。对于讲述自己的“小说的故事”,洛奇知道要冒被视为“自恋”和“自大”的风险,但有些故事因为“其若干奇特的、非同寻常的性质而值得一讲”,比如他的小说《作者,作者》的故事。《作者,作者》与其他几部写亨利·詹姆斯或从亨利·詹姆斯获得灵感的小说几乎同时于2004年出版,在文坛掀起不小的波澜,也给他本人“带来痛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所以,洛奇也将《亨利·詹姆斯年,或时间即一切:小说的故事》一文称为“小说家的故事”,它所谈论的是小说家耗时几年的创作,其中许多内容是自传性趣闻轶事。洛奇希望此文对更为清晰地从心理、社会、经济方面了解21世纪初期的作家职业以及创作过程本身,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和价值。[16]文中写道,由于种种原因,图宾的同一题材传记小说先于《作者,作者》出版,这极大地影响了对后者的接受和评价,因此洛奇发出“时间即一切”的感叹。除了披露《作者,作者》一书的酝酿、创作和读者接受过程中的苦乐,《亨利·詹姆斯年,或时间即一切:小说的故事》一文也没有忘掉小说类型学或者小说诗学的探讨,文中分析了传记小说兴起的原因,它的特征,以及它与历史叙事和传记叙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以上“概述”只是了解本书内容的一个线索。洛奇睿智的语言、富于启发性的论说、深入浅出的阐释、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尽现于本书精选的各篇论文。
本书各篇文章的“概要”,除了《亨利·詹姆斯年,或时间即一切:小说的故事》之外,均为本书编者所加。书中所有注释,除了注明“译者注”或“编者注”,均为原作者所加。
因为原文注释中提到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没有对应的中译出版物,若将其译为中文往往反而令读者因无法还原为英文而失去查找文献的线索,故本书保留了所有论文的英文原注,只有少数篇目的注释被译为中文,但也保留了英文原注,使其以双语形式呈现。
书中部分专名,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保留了不同译者的不同译法。
罗贻荣
2017年10月于青岛
[1] David Lodge,Language of Fi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ⅩⅢ.
[2] David Lodge,Language of Fi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Ⅺ.
[3] 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1,pp.55-68.
[4] 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1,p.Ⅸ.
[5] 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1,p.Ⅹ.
[6]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London:Edward Arnold,1979(reprint),p.viii.
[7]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London:Edward Arnold,1979(reprint),p.Ⅹ.
[8]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London:Edward Arnold,1979(reprint),p.Ⅺ.
[9] David Lodge,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reprint),p.Ⅷ.
[10] David Lodge,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reprint),p.Ⅸ.
[11] David Lodge,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reprint),p.Ⅹ.
[12] David Lodge,Write on,London:Penguin Books,1988,p.Ⅸ.
[13] David Lodge,Write on,London:Penguin Books,1988,p.Ⅹ.
[14] David Lodge,The Practice of Writing,Secker&Warburg,London,1996,p.Ⅸ.
[15] David Lodge,Lives in Writing,Harvill Secker,2014.
[16] David Lodge,The Year of Henry James:The story of a novel,with other essays on the genesis,composition and reception of literary fiction,Penguin Books,2006,pp.Ⅺ-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