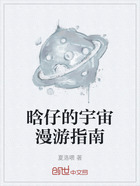
第14章 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无厘头的量子场
讨论这个问题时,咱们先从牛顿聊起。那时候他认为宇宙就是由空间、时间和小颗粒般的粒子组成的。有趣的是,这个简单明了的框架后来被打破了。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登场时带来个新玩意儿——电磁场。你也许没想到,从这时候开始世界不再是单纯的粒子世界,变成了粒子与场共存的奇妙组合。等爱因斯坦带着狭义相对论出现时,直接把空间和时间捏成了时空这个概念,这时候宇宙配方变成了时空引力场、电磁力场加粒子的大杂烩。
真正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广义相对论时期。爱因斯坦直接把时空和场划了等号,这下宇宙配方表只剩两行字:场和粒子。不过上期结尾咱们卖了个关子,物理学界还藏着个没出场的狠角色。
现在该请出咱们今天的主角了。量子力学这个20世纪诞生的怪咖,和优雅的广义相对论简直是水火不容。你看,广义相对论就像块浑然天成的翡翠,爱因斯坦单枪匹马就雕琢出这套解释引力与时空的完美理论。但量子力学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它像是几十个工匠用零碎边角料拼贴的百衲衣,经过无数实验才逐渐拼凑成型。
别看量子力学长得磕碜,人家可是实打实的实力派。你手里的手机能正常使用,多亏了它撑腰。但气人的是这理论都一百多岁了,普通人还是像看天书似的摸不着头脑。市面上量子力学科普多如牛毛,这次咱们换个新鲜角度,用三个关键词带你入门:间断性、测不准、纠缠性。先说说第一个关键词...
现在咱们要说说量子力学的破壳故事了。1900年的某天,有个叫普朗克的老先生正跟实验室的烤炉箱子较劲——他想算明白这个热烘烘的箱子里到底装着多少电磁波。数据倒是测出来了,可要凑出个公式来匹配实验结果,简直比炖锅里的土豆还让他焦头烂额。
这老哥当时肯定没料到,自己随手耍的数学把戏会改变整个物理学史。他心一横,把电磁波的能量切成了小包装,就像超市里论袋卖的白糖。最绝的是他还规定:每个能量包的份量得看电磁波的“颜色“,也就是频率高低。具体来说,频率v对应的能量包大小就是e=hv——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公式,后来成了量子力学的出生证明。
你问h是个啥?这可是普朗克从数学缝里硬抠出来的新常数,现在我们都叫它普朗克常数。别看它数值小得可怜(小数点后带33个零呢),整个量子世界的游戏规则全攥在它手里。就像你玩电子游戏时屏幕里最小的像素点,h决定了我们宇宙能量分割的最小刻度。
当时整个物理学界都被这操作惊掉下巴。要知道那时候大伙儿都坚信能量像流水般连绵不绝,突然有人说能量是论包卖的,活像在菜市场卖活鱼。连普朗克自己都觉得这只是个权宜之计,纯粹为了应付实验数据编的数学故事,根本不敢当真。
没想到五年后有个专利局小职员掀开了魔术师的幕布。1905年,爱因斯坦在寄给《物理年鉴》的三篇论文里,把第三篇的C位留给了光量子理论。他指着普朗克的能量包说:“别当数学工具了,人家真真实实存在!“后来物理学家们翻黄历时才惊觉,原来量子力学的生日该定在爱因斯坦拍板的这一天。
咱们接着说这出科学悬疑剧的转折点。老爱当时指着光电效应这个怪现象说:“你们都被常识骗了!光压根不是连绵不绝的波浪,而是噼里啪啦的粒子雨。“这事儿得从金属板被光照会喷电子说起——就像烤热的铁锅会溅油星子,可怪就怪在油星子溅不溅跟火候大小没关系。
当时的物理教科书全被这现象整懵了。按常理推断,微弱的光线就像毛毛雨,虽然雨点小但下得久总能打湿衣服;强光好比倾盆大雨,自然更容易淋透。可实验结果啪啪打脸:紫光(高频)就算像萤火虫那么微弱,照样能激出电子;红光(低频)哪怕亮得像探照灯,金属板愣是纹丝不动。
爱因斯坦这时候掏出普朗克的能量包理论,就像魔术师亮出压箱底的道具。他打了个绝妙比方:想象你站在瀑布底下接金币,能不能接到钱根本不看瀑布有多宽,全看每个金币够不够分量。要是每个金币都轻如纸片,就算整条河都是金币也砸不出水花;反过来哪怕只有几枚金币,只要个个沉得像秤砣,照样能砸得你手疼。
老爱突然想起普朗克那个能量包的点子,眼睛都亮了——这不就对上了嘛!每个光粒子(后来叫光子)的能量就像不同面值的硬币,紫色光子是百元大钞,红色光子是五毛硬币。金属板里的电子就像自动售货机的投币口,不到指定面值死活不吐货。所以管你红光多耀眼,五毛硬币投再多也买不到饮料;紫光再微弱,只要有个百元钞“叮当“一响,电子立马蹦出来。
这解释最绝的是把物理学家们奉为圭臬的连续性概念砸得稀碎。就像突然告诉你,瀑布根本不是水流而是玻璃弹珠雨,每个弹珠的大小还由颜色决定。当年多少教授看着论文直拍大腿:“我们被波动说骗了三十年!“从此,量子力学这头怪兽才算真正冲出牢笼,在物理世界横冲直撞。
咱们接着说这出科学连续剧最精彩的转折。老爱扔出的光子理论就像往池塘里砸了块板砖——整个物理学界的水花都溅起来了。当时那些白胡子教授们气得直哆嗦:“这毛头小子说光是一粒粒的?那我们苦心经营几十年的电磁波理论算什么?“
最戏剧性的是1905年的学术圈分裂现场:教授们捧着相对论论文啧啧称奇,转头看见光子理论就直摇头。有个大佬甚至在推荐信里写:“这年轻人聪明绝顶,就算他偶尔犯傻(比如那个荒谬的光子假设)也值得原谅。“简直像在说:“我家孩子虽然爱说胡话,但成绩还是好的。“
但最打脸的还在后头。当年那些摇头叹气的教授们,五年后却亲手把诺贝尔奖章挂在他脖子上——就为了他们曾经嗤之以鼻的光子理论!这反转比八点档电视剧还精彩。不过老爱自己可能更想要相对论的诺奖,但谁让评委们当时被量子概念吓得腿软呢?
这下可捅了科学界的马蜂窝。光怎么既像水波般连绵,又像弹珠般粒粒分明?好比说你家养的猫,平时是毛茸茸的宠物,关灯后突然变成无数跳蚤在蹦跶。物理学家们集体抓狂:我们研究了三百年的光,原来是个精分患者?
要解开这个死结,得把整个物理学推倒重来。就像要解释为什么冰雹既能堆成雪人(波动性),又能把车砸出坑(粒子性),非得发明套全新的语言不可。这时候量子力学才真正拉开序幕,等着玻尔、海森堡这群怪才来搭建它的奇幻大厦。
好的,咱们现在要聊聊玻尔怎么把量子理论从光的世界拽进了原子的宫殿。这事儿得从原子结构的“太阳系模型”说起——当时卢瑟福刚用α粒子轰金箔的实验证明,原子确实像个微型宇宙:中心是沉甸甸的原子核(占99.9%质量),周围是轻飘飘的电子绕圈,就像行星绕着太阳转。但这个模型有个致命bug,按经典物理的剧本,绕圈的电子会像漏电的灯泡,不断辐射电磁波,能量越漏越少,轨道越缩越小,最终“咣当”撞进原子核——整个原子会在亿分之一秒内坍缩!可现实中的钠灯明明稳定地发着黄光,辣椒也千年如一日地红艳艳,这明显和理论对不上号。
更诡异的是物质的光谱。就像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指纹,不同元素燃烧时发出的光总是固定几种颜色,比如钠是明黄色双线,氢则有红蓝绿紫四条线。这好比说钢琴家弹琴,明明有88个琴键,他却永远只按固定的四个键。经典物理学家们集体懵圈:电子既然能在任意轨道上跳舞,为什么只挑特定频率的光来发射?
这时候玻尔带着他的量子魔法进场了。这位丹麦天才做了个石破天惊的假设:电子绕核的轨道根本不是随便什么尺寸都行,必须满足某种“量子条件”。就像宇宙给原子装了隐形的旋转楼梯,电子只能站在特定的台阶上——这些台阶对应的轨道半径,得让电子的角动量是h/(2π)的整数倍(h就是普朗克常数)。用大白话说,电子在原子里的活动范围被量子化了,只能住进“单人间”“双人间”这类特定楼层。
更绝的是玻尔规定:当电子乖乖待在指定楼层时,就像穿了滑板鞋,既不摩擦也不发光(违反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但符合实验观测);只有当它从高层跃迁到低层时,才会像跳楼机坠落般,把多余的能量打包成光子甩出去。这个光子携带的能量,正好等于两个楼层之间的价差(E=hv)。反过来,要是电子想上楼,就得吞掉个能量合适的光子当门票。
举个栗子,氢原子就像栋四层小楼。当电子从三楼(n=3)跳到二楼(n=2),甩出的光子恰好是红光(656纳米);从四楼(n=4)直坠二楼,就发蓝绿色光(486纳米)。这完美解释了氢原子光谱里那些神秘线条的来历,就像给每个能级跃迁贴上了条形码。
但最让老派物理学家们拍案惊奇的是,玻尔模型竟能算出里德伯公式里的神秘常数!这个困扰光谱学二十年的数字,居然被玻尔用普朗克常数、电子电荷和质量拼出来了,精度堪比瑞士钟表。当时有个段子说,当玻尔在论文里写出这个推导时,连打印机的油墨都惊得忘了干。
当然这模型也有硬伤,比如解释不了复杂原子的光谱,更说不清为什么电子非得遵守这些量子规则。但就像第一架莱特飞机,虽然飞不高,却证明了人类能挣脱地面——玻尔证明了量子理论不仅能解释光,还能统治微观世界。他给后来者留下把金钥匙:物质世界的离散性不仅存在于能量包里,更深深烙在原子结构的基因中。
从此,量子革命从光电效应的边疆,正式攻入了原子王国的都城。物理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想要看懂宇宙这本天书,得先学会用量子的语法来朗读。而玻尔,正是那个为旧世界敲响丧钟,又为新世界拟定宪章的先知。
那为什么原子里的光不是五颜六色都有,而是固定几种颜色呢?
为什么原子的光线像用尺子量过似的,只在特定位置出现,而不是连成一片呢?
用课本里的话说——为什么光谱是分立的而不是连续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物理学家几十年,就像你盯着拼图找不到最后一块那样难受。
这时候玻尔来了,他做了件特别反常识的事——拍脑袋假设!
他突然想到:如果电子的能量像超市货架上的罐头,只能摆放在固定位置,而不是随意堆放呢?就像普朗克说光的能量是一包一包的,电子能量说不定也是打包好的。
你猜怎么着?所有计算结果突然都对上了!
重点还是“打包“这个概念,不过这次不是光,而是电子自己把自己装进了能量罐头里。
更绝的是,玻尔说电子只能在离原子核固定距离的轨道上转圈,就像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必须卡在轨道槽里。这些轨道间隔由普朗克常数这个“宇宙尺子“精确测量。
最魔幻的是“量子跳房子“——电子能突然从某个轨道消失,瞬间出现在另一个轨道,中间过程?不存在的!就像你眨眼时画面突然切换。
每个轨道对应特定转速,转速决定发光颜色。既然电子只能待在指定轨道,自然只能发射固定颜色的光。
靠着这套“轨道套餐“理论,玻尔不仅解释了已知光谱,连还没观察到的光线都能预言,准得像天气预报。
但你肯定要问:凭什么只能有这些轨道?电子跳来跳去到底怎么操作的?
在玻尔的研究所里,大家像在对付一团乱麻,拼命想给原子世界定规矩。有个德国小伙子海森堡,他带着矩阵数学这把钥匙,终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海森堡越想越不对劲:凭啥电子非得按人类能理解的方式运动?就像你家猫主子突然消失又出现在冰箱顶上,电子凭什么不能玩瞬移?他干脆把笔一摔——要是电子只有在撞到东西时才显露行踪,就像路灯只在你经过时才亮起来呢?如果两次碰撞之间,电子就像被橡皮擦抹掉的铅笔痕迹,根本没有固定位置呢?
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让他连夜开始算数。结果算出来的东西让所有物理学家头皮发麻:你永远没法像追踪足球飞行轨迹那样,精确描绘电子每分每秒的位置。就像监控摄像头只能拍到小偷进出银行的瞬间,电子也只在与其它粒子“肢体接触“时才在照片上留下残影。这成了量子力学的第二条铁律——世间万物就像打水漂的石片,只有在触碰水面时才真实存在。
最烧脑的是这种“遇事才现身“的设定。电子压根不是持续存在的实体,而是由无数个碰撞瞬间串起来的闪光项链。就像你刷短视频时,画面其实是由每秒60帧的静止图片快速切换形成的幻觉。当没人观测时,电子就像被拔掉插头的投影仪,彻底消失在黑暗里。
海森堡用数学表格(后来叫矩阵)记录这些闪烁的瞬间,但计算过程比解开缠在一起的耳机线还麻烦。这时候25岁的狄拉克登场了,这个总爱穿三件套西装的天才,把量子力学从菜市场讨价还价变成了五星级酒店的点单系统。他发明的符号就像乐高积木,让所有人能轻松搭建量子世界。
经狄拉克改造的理论有多绝?就像把杂乱堆满零件的车库,整理成宜家样板间——每个公式都严丝合缝,每个概念都各归其位。如今从造芯片的工程师到研发新药的化学家,每个人都在用狄拉克的“量子乐高“说明书。在这个体系里,连一粒灰尘都被定义为抽象空间里的数学舞步,跳着永不重复的华尔兹。
想象你网购盲盒,拆开前连卖家都不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量子世界里的物体就像这种神秘盒子,除了包装上标着“质量500克“这种固定信息,其他属性都像薛定谔的猫似的飘忽不定。只有当快递员(其他粒子)暴力拆箱的瞬间,位置、速度这些属性才像被摔出来的零件,噼里啪啦随机散落一地。
就像你永远猜不到刷短视频下条推送什么,海森堡发现更恐怖的事实:两次拆箱(相互作用)之间,电子连“可能存在哪里“这种基本信息都没有!就像你手机里的导航软件突然罢工,既不能显示当前位置,也不能预测下一秒位置——量子世界所有物体都在玩这种“捉迷藏PLUS“。
但物理学家总不能两手一摊说“随缘吧“,量子力学给出了独家预测秘籍:虽然算不出电子下次出现的精确坐标,却能像赌场庄家算赔率那样,告诉你各个位置的中奖概率。这彻底掀翻了牛顿时代的“全知台球桌“——以前我们能像计算台球碰撞路线那样精确预言未来,现在却像在拉斯维加斯掷骰子,每次结果都带着老天爷恶作剧般的随机性。
最颠覆认知的是,这种不确定性不是我们仪器太烂测不准,而是宇宙自带的“出厂设置“。就像你永远无法同时看清旋转中电风扇的所有叶片,电子在微观世界根本就是随机闪现在概率云里的光点。我们熟悉的“确定世界“只是假象——好比无数硬币同时抛向空中,当数量多到铺天盖地时,正反面的比例反而稳定得像被精心安排过。
你早上煮咖啡时水面晃动的波纹,可能就是万亿个量子涨落集体表演的谢幕礼。只是这些微观世界的小水花,在宏观尺度被熨烫得比西装裤缝还平整,让我们误以为世界运转得像瑞士钟表般精准。而真相是,宇宙这台精密仪器内核里,每颗螺丝都在跳着即兴的踢踏舞。
量子力学就像拉斯维加斯的超级赌场系统——单个赌徒可能爆穷或暴富(就像电子下一秒出现在哪儿纯看运气),但当万亿赌徒同时下注(好比宏观世界海量粒子),庄家收益却稳定得像用公式计算过。狄拉克的理论就是赌场经理的两把金钥匙:
第一把钥匙能打开“可能性保险箱“,比如提前告诉你老虎机只会吐出樱桃、柠檬、777三种图案(对应物理量的可能取值)。当粒子们像醉汉撞上吧台(相互作用)时,系统立刻弹出账单:这次碰撞最多能刷出能量值A、B、C三种结果。
第二把钥匙更魔幻——它能算出每个结果的中奖概率,就像赌场监控室能预测凌晨三点钟老虎机被拍出777的概率是23.6%。但千万别问“骰子在空中翻转时发生了什么“,系统直接弹窗警告:该问题不存在!就像你无法追问微信骰子表情停在半空时的状态,量子世界根本不在乎两次碰撞间的“空白剧情“。
物理学家们干脆把电子想象成会分身的赌神——它的位置不是固定坐标,而是像赌场大厅飘着的彩色烟雾(概率云)。烟雾浓的地方好比21点牌桌区,十米外都能听见欢呼声(发现概率高);烟雾稀薄处就像厕所走廊,基本逮不到人影(概率低)。
那几十年物理学家们乐疯了,量子方程就像赌场万能密钥,随便什么问题插进去都能“叮“地亮绿灯。最震撼的是破解元素周期表——这相当于用赌场账本反推出了所有鸡尾酒的配方!
十九世纪的化学家就像在美食街开盲盒:发现所有菜品(物质)都由基础食材(元素)组合而成。门捷列夫如同米其林大厨,把氢、氧、铁这些“食材“按特性摆成元素周期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番茄是红色、菠菜会发苦(元素特性成因)。
量子力学登场时,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狄拉克的方程就像厨房中央的智能料理机,按下启动键就自动吐出118种预制菜(元素解)。氢元素是开机默认的基础清汤,铀元素是压轴硬菜佛跳墙,每种元素的酸甜苦辣(化学属性)都对应方程里精确调配的数学香料。门捷列夫那张著名的元素表,本质上就是量子厨房的出菜单——西红柿炒蛋为什么是这个味?因为它是方程第26号解的指定味道(铁元素)!
狄拉克的壮举就像用乐高积木统一了全世界的玩具——他把牛顿的弹珠(粒子)和法拉第的橡皮泥(场)揉成了量子橡皮泥弹珠。这种新型材料既能像弹珠般精准碰撞,又能像橡皮泥无限延展。想象你网购的快递包裹:平时是规整纸箱(粒子形态),拆开瞬间却爆出漫天飞舞的泡泡纸(场形态)——电子在两次“拆箱“碰撞间,本就是一团概率构成的弹性泡泡云。
更绝的是,当狄拉克把这套理论套在电磁场上,就像给摩天大楼装上乐高接口。原本连续流动的电磁场,突然分裂成标准尺寸的能量积木块——这直接呼应了30年前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猜想:光能量就像超市卖的预包装糖果,只能整袋买卖不能散称。量子场论就这样把世纪初零散的灵感碎片,拼成了浑然天成的乐高城堡。
从此物理学家有了万能说明书:世间万物都是“量子橡皮泥“捏出来的。电子是电磁场的标准积木块,希格斯粒子是质量场的限定手办。就像你在宜家买家具,所有复杂结构都分解为15种基础板材(标准模型的15种场)。中子不过是夸克场+胶子场的组合套餐,好比用木板A和螺丝B拼出马尔姆抽屉柜。
最妙的是这套系统自带“光速合规认证“(兼容狭义相对论)。但遇到引力这种“上古手工家具“就傻眼了——量子乐高插不进榫卯结构,这留待未来大师解决。如今我们知晓,头顶星空本质是15种量子橡皮泥在宇宙画布上的即兴涂鸦,每次星光闪烁都是场与场交换乐高积木的沙沙声。
量子力学揭示的真相,就像人类第一次看清4K屏幕的像素网格——从前我们以为钟摆振幅是莫奈油画般丝滑渐变,结果发现宇宙本质是马赛克拼图画风。想象你手机屏保里的动态摆钟:经典物理视角下,钟摆像丝滑液体在5-6厘米间流淌;量子视角却像开了显微镜,发现摆锤其实在玩《我的世界》——每次摆动都是像素块在固定格点上瞬移!
这颠覆性如同发现钢琴的惊天秘密:你以为手指能在琴键上滑出连续音高,实际上每寸移动都在触发不同琴槌(能级跃迁)。量子世界根本不存在“五点零零一厘米“这种状态,就像钢琴发不出介于do和re之间的暧昧音符。当钟摆从5cm量子跳到6cm,就像游戏角色在《超级玛丽》里瞬移过管道,中间根本没有“跳跃过程“的动画帧。
量子场论更狠,直接把宇宙改造成巨型LED幕墙——那些我们称为“粒子“的,不过是特定像素点突然亮起的闪光。就像你刷抖音时,以为看到连贯舞蹈动作,实际是每秒六十帧的静态画面欺骗了眼睛。希格斯场是常亮的背景灯,电子是某个坐标突然炸开的像素烟花,而你的观测行为就像突然按下屏幕截图键,强行把流动的光量子凝固成.jpg文件。
最魔幻的是测量行为本身——它就像在川流不息的地铁口突然拉闸断电,等灯光再亮时,所有乘客(量子态)都定格成雕塑般的确定姿势。我们永远拍不到地铁运行中的模糊残影(叠加态),只能得到一张张突兀的“量子快照“。这就是为什么钟摆测量值总定格在某个确定数,不是因为它原本如此,而是你的观测强行给它拍了证件照!
现在看元素周期表,简直就是量子宇宙的像素配色方案——氢原子是1号像素点发出淡蓝幽光,铁原子是26号像素绽放金属光泽。门捷列夫当年排列的不仅是元素,更是宇宙显示屏的发光编号。而标准模型的15种场,对应的就是屏幕制造商预设的15原色发光二极管,所有物质图景都是这些基础像素的排列组合。
所以当物理学家说“自然界存在基本分立性“,等于揭穿了宇宙是个超级体素游戏——我们以为的丝滑运动,不过是造物主显卡渲染的障眼法。就像你摸到的光滑手机屏,放大千倍全是颗粒分明的RGB晶格。量子力学扯下了现实世界的“高清滤镜“,让我们看见万物皆由无数闪烁的量子像素构成,每次眨眼都在刷新宇宙的显示帧率。
但是量子力学说,在5厘米到6厘米之间,摆动的幅度其实有明确数量的可能值。所以关于钟摆,我们没掌握的信息其实不多。
第二个关键点是关于电子的不确定性。比如量子场里的粒子或光子,根本不会按固定路线运动,只有撞到其他东西时才会在某个位置现身。到底啥时候出现?具体在哪儿?咱们根本没法确定。量子力学把这种不确定性刻进了世界底层逻辑,未来确实没法被精准预判。在这个微观世界里,万物永远在随机波动,所有参数都在不停抖动。
第三个发现最烧脑也最颠覆——量子力学根本不描述事物本身。它只讲事物怎么出现,怎么互相影响。不说粒子在哪儿,只说粒子之间怎么感知对方。就像亚里士多德讲的,我们只能感知相对速度:在船上说船速,在岸上说地面速度。量子力学把这个相对性推得更狠——物体的全部属性都只在与其他物体的关系中成立。大自然只在互动中构建世界。这不是说事物发生了关联,而是说关联本身就是事物的全部。量子世界不是物体的世界,是事件的世界。
举个接地气的例子帮你理解:比如朋友给你介绍相亲对象,你想知道对方颜值如何?介绍人说:“这个我说不准,但每个路过的都会回头多看两眼。“问收入情况?
介绍人接着说:“收入多少我也说不好,但听说他经常在高端会所进出。“你想知道谈吐气质如何?对方回:“这个也不清楚,不过他家里整面墙都是书。“这时候你大概会脑补出个颜值高、收入丰厚、谈吐不凡的形象。但仔细想想,你连他真实长相都没见过,具体收入金额不知道,谈吐风格更无从验证——就像在量子世界里,我们永远没法直接“看清“事物本质。这不是观测设备不够先进,而是自然法则本身的限制。
我们只能通过碎片化的事件拼凑微观图景。比如把电子想象成坚硬小球,这完全是人脑自行补全的画面。事实上,根本没人能说清电子“真实模样“。要是觉得难以接受,不妨思考日常经验:我们说某物长什么样,至少得有颜色特征吧?是黑是白还是彩色?但颜色本质是物体反射的光波频率——电子既不发光也不反光,所以它连颜色属性都不具备。既然能接受电子没有颜色,为什么不能接受它也没有其他常见属性?
说真的,我当初也纠结了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电子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西“。就连“电子“这个名字都是人造的标签,我们实际接触的从来不是实体,而是实验室里各种碰撞痕迹和数据曲线。为了解释这些现象,人类创造了“电子“这个概念,结果反而被困在“它到底长什么样“的思维陷阱里。
这就好比我们创造了“星期一“这个概念——你能说星期一本身长什么样吗?量子力学逼着我们换种活法看世界:别盯着某个静止状态琢磨,要盯着事物互动的全过程看。每次粒子碰撞、每次能量交换,这才是真实世界发生的剧情。物体的所有特征只在碰撞瞬间闪现,就像游戏角色只在触发电击时显示属性值。
如今科学家们每天用着这些方程时,依然觉得背后藏着大谜团。这些公式不画物质本身,只画物质之间怎么掰手腕较劲。我总在想:那宇宙最底层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从实验室到哲学课堂,这个问题烧脑烧了快一百年。你看,相亲时别人给你拼凑的零碎印象,和科学家用数据拼凑的电子画像,本质上都是管中窥豹。
但科学最酷的地方就在这儿——就算知道明天可能有新理论推翻旧认知,今天照样全力以赴搞研究。或许量子力学难懂不是它的错,而是我们想象力不够。宇宙凭什么要按人类能理解的方式运转?但人类偏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死磕精神才催生出科学火种。就像你听相亲介绍时,明知信息不全还是忍不住脑补完整形象,我们面对宇宙奥秘时,同样控制不住探索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