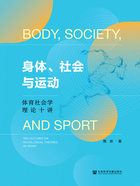
五 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前面我们讨论了体育是如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结合的,又是如何被社会生活和身体经历描绘、诠释和改写的。无论是从社会制度上还是从身体的角度,体育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研究体育的时候,必须把体育作为一种和其他社会系统互相依存的社会系统和文化现象来看待。这需要我们用社会学的视野来探索体育,用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体育,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体育。体育社会学主要是从社会本质上来把握体育的特征、功能、手段、途径,目的在于促进体育运动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最终为人的发展服务。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包括:(1)体育社会现象;(2)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3)体育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4)体育社会问题;(5)体育形态;等等。不仅如此,体育社会学还为体育研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这为体育从身体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理论体系来看,体育社会学理论有三个主要视角:一是宏观理论视角(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型构理论、结构化理论);二是微观理论视角(如社会行动理论、符号互动理论);三是批判主义视角(如批判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当然这三个主要视角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理论本身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反思与批判中不断地自我修正和发展。
(一)宏观理论视角
从宏观的角度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体育社会学最经典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研究倾向。一方面,社会学家想通过体育制度的发展来反映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进一步探索体育如何嵌入社会生活并对社会稳定与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结构功能主义为体育宏观层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基石。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认为体育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向体育参与者传递着某种社会价值观,并维持着社会的秩序。但是,他们也强调体育对社会的功能只有在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结合中才能体现出来,这些要素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等。首先,体育是一个次文化体系(sub-cultural system),它可以教会人们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与道德标准,这也体现了体育的社会情感功能。其次,体育实践可以通过集体的展示将社会成员整合起来。最后,体育也是一种社会角色塑造的工具,它会影响个体社会角色的学习过程。社会学家要探讨的是体育如何帮助社会、社区、组织以及团体平稳地运转,同时也探讨个体如何在参与体育的过程中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一系列的研究充分体现了“社会学试图用一个范式和过程来反映社会如何塑造个人”的研究思路。在结构功能主义者的视野中,社会结构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社会事实(包括运动规则、规律)是操纵人类行为(体育活动)的“看不见的手”,形成了(体育运动的)有机秩序。
对体育制度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型构理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与结构功能主义静态的系统论不同的是,型构理论强调了社会(发展)过程,并认为社会是在历史过程中由互相依靠的人群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构成的,这为更好地理解体育化(sportization)过程奠定了基础。比如,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现代体育是如何在历史、经济、政治和情感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体育参与如何在一个社会过程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体育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了职业化、商业化的变迁?以及体育暴力的产生与控制问题,体育和国家主义、殖民主义的关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媒体、消费主义对体育的影响等。这些研究试图从特殊的现象中找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对这些规律进行总结和归纳,这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经典思路。
如果说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秩序的和谐,冲突理论则强调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及其对社会运转产生的影响。冲突理论为理解体育中出现的剥削、压迫、冲突、矛盾、不平等、排斥、分层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体育是由那些掌握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人所组织和赞助的,目的是确立一种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竞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体育渗透于精英阶层并巩固其特权,同时体育也成为经济剥削与压迫的工具。体育运动员在体育参与中不自觉地建构了一种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需求的社会结构。运动员对于自身劳动力控制的缺乏是导致体育异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体育不平等现象出现的根源。当然,很多社会学家也从性别制度、种族制度角度讨论了体育冲突、矛盾和不平等现象的社会根源。比如,女性主义者认为体育是以宣扬男性文化为主并被男性控制的社会制度,这是造成体育中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因此他们认为要消除体育中的不平等就要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体育模式进行抵抗,并重新建立体育秩序。种族制度也是社会学家研究体育冲突、矛盾、不平等现象的出发点。他们认为种族歧视是体育中的制度性缺失。比如,白种人通过自己在体育比赛中的优秀表现可以得到社会的肯定;但是对于有色人种来说,获得社会认可的可能性小得多。社会学家认为,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差别,而是制度的阻碍。除此之外,残疾人、贫困人群、青年人、老年人的体育参与都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他们试图探讨社会制度如何导致了体育现象中的分层、不平等问题,而这种不平等又对社会产生了哪些危害。这种研究方向充分反映了社会学视野关注边缘性和社会危机的特点。
(二)微观理论视角
从微观角度了解并诠释体育行动/互动过程所产生的意义是体育社会学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社会学除了倡导要宏观地把握系统规律,进行预测以外,也要求社会学家对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进行充分理解并做出意义诠释。
社会行动理论为从微观层面探讨体育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了分析框架。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体育不仅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更偏重心理学的范畴),更是一种社会行动,是一种有意向性的身体行为。正如韦伯所观察到的,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社会行动的不断理性化,体育运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逐渐理性化。“体育专业化”“商业化”“职业化”“科技化”都是现代人(社会)对体育运动的追求不断理性化的表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人抱怨现代体育开始丧失以往的魅力。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它的魅力在哪里呢?其魅力就在于,体育参与过程会生成对个体/群体/国家/社会的意义。例如,根据体育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对巴林人斗鸡的田野调查,他发现斗鸡活动对于巴林人来说不仅是金钱性质的赌博(功能性的),还是有关“生与死”的社会存在与文化隐喻。
体育参与过程中意义的产生是通过互动完成的,在互动中又会产生新的体育符号、仪式,以及身份认同。符号互动理论为解释这些问题,如“运动员、教练、体育观众以及其他体育参与者的互动”“人们如何定义自己或定义别人为运动员”“人们如何在体育参与中实现自我存在意义或被剥夺自我存在的意义”等提供了分析框架。一些社会学家强调要从局部与个体的研究来反映体育的真实特点,并质问这些特点是如何被人们创造出来并影响他们的体育认知与行为的,总之要从微观层面去理解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体育行为。比如,研究运动员在不同阶段(训练、竞赛以及退役后)的社会身份以及自我认知;体育参与者是如何把体育行为和其他社会因素(工作、家庭、教育、传媒等)结合在一起并进一步影响自己的体育参与的;体育参与者与体育组织(政府、社团、小团体)的互动;人们在体育过程中的自我满足、自我意识、自我认知等。这种从小的社会点入手去理解大的社会现象的方法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主流。
(三)批判主义视角
“批判性思考”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特质,批判主义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也已然成为一种揭示体育社会文化现象的核心视角。无论是文化研究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还是最近兴起的物质身体文化研究,都保持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在审视体育社会文化现象。
首先,解释和研究体育亚文化问题。比如,体育如何维持亚文化圈的行为模式?体育亚文化圈如何整合它的成员从而实现他们追求的目标?体育亚文化圈成员是如何适应主流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对体育亚文化功能的分析是围绕着体育失范来展开的,如越轨、欺骗、药物滥用以及兴奋剂问题。另外,一些社会学家也非常关注体育亚文化是如何抵抗主流文化的压力的,如足球流氓文化、体育赌博文化、体育暴力文化的产生与控制等都是西方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社会学家独有的危机感和灵敏的研究触角把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非主流的、隐藏在深处的并以为是想当然的体育现象与体育问题挖掘了出来,并给人们以警示。
其次,全球化和体育霸权的研究。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以西方文明为主导、以工业和商业利益为核心、以西方产品(包括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推广为目的的过程。社会学家观察到体育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不少作用,具体表现在现代体育的形式、内容、规则按照西方的模式逐步统一。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奥运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但同时,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和民族也在倡导体育的民族性和多元化以强化地区的差异和民族的自我认同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跆拳道、柔道等东方运动在西方世界的流行,并成为奥运项目。因此现代体育的发展过程被看作全球化和多元化相互交织、并行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学家关注到:(1)东、西方体育文化对立的消失,多元化的出现;(2)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3)新兴体育文化的出现;等等。但一些学者也在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的体育霸权问题。他们注意到长期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坛上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缺少足够的话语权。西方价值观念、西方文化、西方体育模式和规则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身上,强权体育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全球性的比赛项目设置和规则制定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进行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体育项目则很难迈进世界体坛的赛场等。总之,全球化的思路越来越受到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青睐,这和体育自身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体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再次,体育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曾经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比较分散、无系统性的研究派别,但是现在文化研究已经是学术界一个成熟的人文学科。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当下的流行文化以及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虽然文化研究跨越领域非常多,但是其分析模式基本围绕着“解构”为核心,也就是用批判的态度揭示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被人们遗失或忽视的问题。体育作为一种流行文化,长时期没有得到文化研究的关注。同样,在传统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中,体育一直被社会学家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形态进行论述,即使是对体育文化的论述也是从历史、社会过程以及人类学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文化研究并没有进入体育研究的学科正统。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结构主义和身体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大量应用,体育文化研究(这里强调的是“体育的文化研究”,而不是“体育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视角,被用来解析当代体育现象隐藏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如大众媒体对体育的影响、球迷现象、女性体育问题、体育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体育身体与权力关系等。体育文化研究方法强调述说和倾听,以个人或集体的经历为主,以批判的态度分析问题,它并不强调系统性和固有的研究范式,而是鼓励研究的多样性,这和传统社会学实证方法论有一定的区别,却越来越受到年青一代研究者的青睐。文化研究的引入,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为层出不穷的当代体育现象提供了研究工具,也为体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最后,物质身体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在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物质身体文化研究是为了应对自然科学对身体运动机能研究(过度)科学化倾向(bio-scientization),以及传统社会学研究对运动身体过度抽象化的阐释,物质身体文化研究者提出应该从运动身体的物质性、经验性、具身性、人文性等综合特点角度去考察身体运动方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权力。他们注重对现实世界中运动身体及其多元表现形式的研究,揭示身体运动对社会分裂(阶级、性别、民族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时,也关注身体运动发生的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背景,考察身体在运动中的经验、表达与呈现,以便深刻透视体育文化的全貌。物质身体文化研究还强调体育社会学研究需与行动反思及社会变革紧密相连,因而带有显著政治批判色彩。
我们探讨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以及在社会学视野中体育被阐释、呈现的角度和途径。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开辟了新的视角来描述和理解在特定社会文化下产生的和体育有关的行为、态度、互动、冲突、权力、权利以及体育(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同时为体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系统的研究方法。但是当遇到具体的问题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去发现并分析问题。社会学理论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基本的框架:用批判性思维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释现象、得到启示、发展理论。在以下各讲中,我们就要具体介绍各种社会学理论以及它们在体育研究中的应用。
[1] 这里的“体育”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而不是专门指体育教育(PE)。
[2] Coakley,J.,Sport in Society:Issues and Controversies(New York:McGraw-Hill Publishing Co.,2001),p.20.
[3] 在本书中采用体育的广义概念。
[4] 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59~61页。
[5] 约翰·洛克:《教育漫话》,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6] Ferguson,A.,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Edinburgh:A.Millar & T.Caddel,1767).
[7] Loy,J.,“The Nature of Sport:A Definition Effort,” Quest,1968,10(1):1-15.
[8] Caplow,T.,Principles of Organisation(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4).
[9] 这里更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Coakley,J.,Sport in Society:Issues and Controversies(New York:McGraw-Hill Publishing Co.,2001),p.3.
[11]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6页。
[12] Mangan,J.A. and R.J.Park,“Introduction,” in J.A.Mangan and R.J.Park(eds.),From “Fair Sex” to Feminism:Sport and Socia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Eras(London: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1987).
[13] Houlihan,B.,“Politics and Sport,” in J.Coakley & E.Dunning(eds.),Handbook of Sports Studies(London:SAGE,2000),p.213.
[14] Houlihan,B.,Sport,Policy,and Politics:A Comparative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7).
[15] 拉·英·斯卓姆:《体育与政治》,徐刚生译,《体育文史》1987年第1期。
[16] von Clausewitz,Carl,On War(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176.
[17] 《奥运会:体育赛事还是赚钱机器》,http://finance.sina.com.cn/financecomment/20040813/163594765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0月10日。
[18] 周成:《体育赛事旅游的经济学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6~48页。
[19] 杨汛:《上半年本市旅游总人数总收入双增长》,《北京日报》2009年7月20日,第1版。
[20] 《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仍占固定资产投资一半以上》,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70125/0813328046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0月10日。
[21] Coe,S.,“London 2012 Was a Once in a Generation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Everything That Makes Britain Great,” Speech at Europa Press Breakfast Event,Madrid,2013.Retrieved from GOV.UK: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ord-coe-in-madrid-london-2012-was-a-once-in-a-generation-opportunity-to-showcase-everything-that-makes-britain-great,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月15日。
[22]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2012 London Olympics [Infographic],” http://www.visualinformation.info/the-economic-impact-of-the-2012-london-olympics-infographic/,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0月10日。
[23] 陈珊:《伦敦奥运的经济遗产》,《北大商业评论》2013年第4期,第97~101页。
[24] 潘寅茹:《巴西冲刺“奥运经济”》,《当代县域经济》2016年第9期,第6~7页。
[25] 卢嘉鑫、张社平:《体育产业发展——理论与政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
[26] 《2020年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提前完成十三五计划「组图」》,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0979160186325479&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0月10日。
[27] 《国家体育总局:预计到2035年体育产业总量占GDP比重4%左右》,https://www.sohu.com/a/338162583_561670,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0月10日。
[28] Xiong,H.,Urbanis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Women’s Sport Since 1980:Reconstruction,Stratification and Emancipation(London:VDM Publishing House,2009).
[29] 田小虎:《对体育与媒体关系的认识》,《青年记者》2008年第5期,第34页。
[30] Turner,B.S.,The Body & Society(Second Edi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6).
[31] Delaporte,F.,Disease and Civilation:The Cholera in Paris,1832(Cambridge,MA:MIT Press,1986),p.6.
[32]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and Rea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3] Xiong,H.,Urbanis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Women’s Sport Since 1980:Reconstruction,Stratification and Emancipation(London:VDM Publishing House,2009),p.59.
[34] Hargreaves,J.,“The Body,Sport and Power Relations,” in J.Horne,D.Jary,and A.Tomlinson(eds.),Sport,Leisure and Social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7),pp.139-159.
[35] Hargreaves,J. and Vertinsky,P.,Physical,Culture,Power and the Body(London:Routledge,2007),p.8.
[36] Jarvie,G.,Sport,Culture 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London:Routledge,2006).
[37] Cole,C.L. and M.Orlie,“Hybrid Athletes,Monstrous Addicts,and Cyborg Natures,”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1995,22(3):229.
[38] Hargreaves,J.,Sport,Power and Cul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6),pp.161-181.
[39] Crossley,N.,“In the Gym:Motives,Meaning and Moral Careers,” Body & Society,2006,12(3):25.
[40] Rail,G.,“The Wellbeing Imperative:On Bio-Others,Rescue Mission and Social Justice,” ISSA 2015 World Congress Book of Abstract,Paris Descartes University,Paris,2015,June 9-12,p.1.
[41] Pronger,B.,“Rendering the Body:The Implicit Lessons of Gross Anatomy,” Quest,1995,47:435.
[42] Ransom,J.,“Feminism,Difference and Discourse:The Limits of Discursive Analysis of Feminism,” in C.Ramazanoglu(ed.),Up Against Foucault(London:Routeledge,1993),p.123.
[43]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66页。
[44] Andreasson,J.,“‘Shut up and Squat!’ Learning Body Knowledge Within the Gym,”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2014,9(1):1-15.
[45] 林金玉、熊欢:《农村妇女健康促进的体育行动与策略——基于广东省清远市J村妇女的行动研究》,《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9~19页。
[46] Allen-Collinson,J. and Owton,H.,“Intense Embodiment:Senses of Heat in Women’s Running and Boxing,” Body and Society,2015,21(2):245-268.
[47] 熊欢、王阿影:《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49~58页。
[48] Shilling,C. and Bunsell,T.,“From Iron Maiden to Superwoman:The Stochastic Art of Self-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iant Female Sporting Bod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Exercise and Health,2014,6(4):478-498.
[49] Shilling,C. and Bunsell,T.,“The Female Bodybuilder as a Gender Outlaw,”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and Exercise,2009,1(2):141-159.
[50] 熊欢、王阿影:《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49~58页。
[51]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02页。
[52]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66页。
[53] Fowler,B.,Bourdieu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Sage,1997).
[54] Bourdieu,P. and Wacquant,L.J.D.,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London:Polity Press,1992).
[55]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66页。
[56] Sewell,W.,“A Theory of Structure:Duality Agency,and Transform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2,98(1):1-29.
[57] Huppatz,K.,“Pierre Bourdieu:Health Lifestyles,the Family and Social Class,” in Collyer,F.(ed.),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ocial Theory in Health,Illness and Medicin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5).
[58] 熊欢:《社会学视域下育龄妇女健康体育干预的综合效应与社会机制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83~94页。
[59] 熊欢:《社会学视域下育龄妇女健康体育干预的综合效应与社会机制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83~94页。
[60] 熊欢等:《凡身之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第313~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