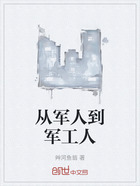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9章 随遇而安
计划经济时代有个特点,凡是有工作的人等于有了组织,而有组织的人就有依靠。
由于长江路被火烧毁房屋的住户中,有不少是饮食公司的职工,所以饮食公司将单位所经营的几家旅馆中腾出了一幢,临时安置受灾户。反正当时住旅馆的旅客不多,客房空闲率很高。
安置受灾户的这家旅馆位于西郊路中段,面对前进菜市场路口,紧邻杨家坪转盘,是一幢四层红砖楼房。一楼用着饮食公司的临时办公室,二、三、四楼安置的都是饮食公司的受灾职工。每一层有二十余间房,左右两头的两户房间是套间,住的是人口比较多的家庭;其余都是单间房,面积大约20多平方米。每间房都有现成的床铺、被子、小衣柜等简单家具。每层楼有一间男女共用的公用卫生间和沐浴房,当时没有厨房,好在饮食公司本身就是做饮食生意的,所以受灾的职工和家属,先被安排在单位的职工食堂就餐,伙食费等关饷时在工资中扣除。后来单位将卫生间旁边的库房改装成公用厨房,大伙才正式自己开伙。
我家被分配在二楼中间临街的一间房,斜对楼梯,有两扇正对前进市场的窗户。父母到百货商店购买了一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住了进去。
由于受灾户的家被火烧光,临时分配栖身的屋子里空荡荡的。很长一段时间,各家各户都买来木材自己学做家具,过道上经常被马凳、泡花占去大半,只能侧身而过。
父亲也自己动手自制家具,当时烧火炉都需要木柴发火,父亲将买来的柴火中比较成型的木料积成下来,又到木材商店买了一批木方和三层板,借来木工工具(自己也做了一些),每天下班后,就在家里自制家具。
有时父亲的同事星期天也来家帮忙,交流在制作家具中的一些体会,相互学习借鉴。记得那时我经常被父亲差遣到五金店购买钉子、刷子、油漆、胶水之类东西。
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才逐渐做好了床铺、衣柜、高低柜、鞋柜、饭桌、椅子等家具,把小小的房间堆得满满当当的,虽然样式比较呆板,但相当结实,一直用了很多年。
位于长江路上父母工作的扬家坪照相馆,也被那场大火烧去了前面的一半房屋。被火烧毁的是临街的营业厅和摄影厅,好在后面那一栋两层楼工作间的主要设备受损不大,但没有摄影厅也无法恢复营业。
照相馆的职工被临时安排在饮食公司所属的各个餐厅上班。父母在餐厅工作了将近一年,直到照相馆的房子修好恢复营业后,才又重回照相馆上班。
我们回渝时学校还在停课,没有学上的小学生们无所事事,经常在街头巷尾东游西荡,饮食公司暂住在旅馆的一群不同学校的职工子弟,很快就混熟了,成了要好的玩伴。
我家暂住的这家旅馆的侧面,是我原来住家所在的长江路边火灾后的那一大片瓦砾,那里给小小的我留有一道阴影。我也曾悄悄的来到废墟的断垣残壁上,试图寻找那个狭小简陋但无比温馨的家园,天真少年的心灵满是伤痕。
那一带后来被清理出来,被一家建筑公司分成了几大块,用来堆放修建房屋用的预制板和河沙。靠近水沟一侧,还有几棵幸存的梧桐树和黄葛树。过了水沟,由街道出面建有长长的几排竹子作骨,蔑席为墙,油毛毡铺顶捆绑而成的棚房,住的是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街道火灾受灾户。整个这片区域,从此被称为“火烧坝”。那里就成了我们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们肆意撒野的玩耍场所。
10月中旬,同学们接到开学的通知,返校后,由班主任组织全校学生清除垃圾,打扫卫生,做了两天力所能及的劳动,学校才复课。
虽然大环境恢复了教学条件,但教室里桌椅损坏得太多,修理了一些,但还有一些没法使用了,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课桌和椅子坐。区教委紧急进行了定购,但新的桌椅的生产制作有一个周期,家具厂不能马上送到学校,于是学校动员男同学自带小凳子来校上课。
父亲便亲自动手,用废旧柴火为我做了一张小凳子,很轻便,每天我和班上的男同学都带小凳子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又带回去(放在教室怕被偷),一直带了三个多月学校才配齐了桌椅。
复课后,学校上课时间并不充裕,偶尔还停课,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所以,那时的小学生课余时间很自由,放学后不用呆在家里做课外作业,家长们也不大担心安全问题,很少管束。所以,每天下午放学后的火烧坝总是聚集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小孩子,打打闹闹,尽兴玩乐。
我在放学后,常常连家门都要不进,一般是站在房门口把书包往离门2米左右的床上一甩,向在走廊斜对面厨房里煮饭的父母打声招呼,便跑到火烧坝找小伙伴玩耍去了。
那时玩过的游戏,能够回忆起来的,主要有几种:
一是捉迷藏(也称占营或逮猫):先是通过石头剪刀布,选出一个倒霉蛋,负责捉人,被选中的小家伙就要自己用双手蒙住眼睛报数,从1数到几十不等(依参加游戏的小孩人数定)。这段数数的时间里,其他人就四散躲起来了。数完数后,开始找人,把所有人全找出来,一局就结束了。在这一局中,第一个被捉到的人要在下一局中负责捉人。捉迷藏从来没出现过捉不完人的情况,因为躲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只要一个个地方挨着的找,总能把人都捉出来。
二是滚铁环:就是用一个铁勾将一个钢筋圆圈滚起来进行比赛,参赛者两个人或者一群人都可以。比赛规则是在速度快慢的基础上,先倒下的为输。这个游戏算是运动量大的一类。
三是“修房子”:就是先用白色粉笔在地上画上线并标上序号,然后单脚将一串石子踢进画好的“房间”里,顺序踢错就算输一局。这是个男女混合比赛,大多数情况下,男生总是输给女生。
四是跳绳:分为单人跳或多人跳,以跳绳花样或者跳绳成功次数定输赢,也是男女混合比赛,也是女生占优。
五是斗鸡(也叫“撞拐子”):游戏规则是一脚独立,另一脚用手扳成三角状,膝盖朝外,用膝盖去攻击对方。直到对方双脚落地,则赢得战斗。参赛人数不定,可以两人赛、三人赛,甚至多人赛。在童年游戏中,这是对抗性最强的游戏。一般情况下,女生基本上袖手旁观。
总之,一帮小孩子蹿上跳下,追逐嬉戏,耍得忘乎所以,从来不会主动回家。家长们下班后也从来不管小孩子们。一般日暮时分,大人们才会扯起喉咙,喊自家的小孩回去吃饭。
即便回了家,我们被家长押着洗了手,抖干净衣服上的泥土沙子,端起饭碗,夹上菜,又会聚在走廊、楼梯口或公用厨房里,同学邻居们边吃饭边摆龙门阵。吃完饭后,把饭碗往灶台上一放,又邀约着一起跑出去耍去了,晚上睡觉又要家长扯起喉咙喊回家。
学校年年都要举办运动会。小学一年级因特殊情况影响没有举行,到二年级,则按惯例举办了学生运动会。
学校的运动会以田径运动和游戏为主,大家踊跃参加,但对争夺锦标兴趣不大。当时有个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也是中国当时竞技体育的核心理念。
可惜学校运动会没有游泳比赛项目。在旅馆暂住的那几年里,我们课余时间最刺激的耍事,要数偷偷下河游泳了。长江边的建设厂码头,每到夏季的黄昏,游泳的人总是人山人海。那时我们一帮崽儿,人小胆子大,根本不知道擅自下河游泳蕴藏的危险,有时甚至等不及到炎热的夏天放暑假,只要学校下午不上课,感觉天气热一点,就经常伙起下长江玩水,乐此不疲。
我们一般是中午等大人们上班后悄悄约起来到河边,在大人们下班前提心吊胆溜回家。回家后小崽儿们个个都装老实,但大人们也不好糊弄,只要一摸娃儿的脑壳发现头发水泡过,或者用指甲在手臂刮一下(皮肤在水里泡久了晒干后,会刮出一道道白色的痕迹),扯过去就打。家长们自然都知道应该怎样收拾明知故犯的小崽儿最有效:那就是除了蔑片,其它大道理一概听不大懂。“喜剧”的还有,只要一家的娃儿遭理麻,左邻右舍立即传染病一般也会响起蔑片声和嚎啕声。
也不是我等顽童打不怕,实在是一天不玩水就心痒难耐。小崽儿些不识好歹,在没课的下午累犯禁令,照常偷偷摸摸地下河戏水。家长们拿不可教的孺子们也没办法。到1968年放暑假时,七一仪表厂的游泳池开放对外营业,游一场2个小时,门票也便宜。出于安全考虑,家家户户的大人们都给自家娃儿办了一张游泳证。从此,下长江游泳的事才被杜绝。
说起体育运动,还有一桩趣事:大约也是三年级前后,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为增加营养,父母在奶品公司订了牛奶,2角2分钱一磅(两瓶),由奶品公司每天早晨定时用汽车送到杨家坪建设电影院广场,订牛奶的人们手持订奶月卡排队等候,送奶员先用圆珠笔在订奶卡当天的日期上划线,然后将牛奶倒到人们自带的瓷盅里。
受母亲差遣,我每天天刚亮就要手持一个大瓷盅,从家中到建设电影院广场去为家人打牛奶。排轮子常常使我失去耐心,所以打好牛奶后我免不了猴急急地一溜儿往回窜,令我恼火的是每回牛奶都会荡出一些。母亲叫我慢点、慢点,可我总管不住自己的腿。
有一次,我打了牛奶回家时,偶然发现有个平端牛奶盅的中年人,扭着屁股甩开大步怪模怪样地走路,又快又稳当。我一时心血来潮,悄悄跟在大叔的屁股后面,疯疯颠颠地模仿了几回。嘿,绝了,牛奶不拨出来了。于是我在路人侧目中硬是把那种高难度的“运动”坚持了下来。直到大约20年后,我才从奥运会的电视转播里弄清楚,那令人发笑的走路姿式叫“竞走”,还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大约是三年级放暑假的一个星期天,一个读初中的陈姓邻居,受大人的委托,带我和另外一个小学生邻居,乘坐电车到解放碑大阳沟农贸市场去为各自的家里买菜。
大阳沟农贸市场很大,菜品非常丰富,买菜的人也很多,但到处都要排队,轮子很长。陈哥叫我们两个小学生分别排好队,他到前面的销售点去看一下情况。殊不知他刚走,我排的这路轮子突然散了,说是这边的菜卖完了。问题是人群一乱我找不到陈哥,他也找不到我,就这样走失了。
那时的我人小鬼大,心里也不怎么害怕,决定自己打道回府。好在那时公交不发达,线路单一,不象现在这么复杂,不容易坐错车。
我故作镇定,一个人乘解放碑到上清寺的1路电车,上车后还主动拿出母亲给我买菜的钱买车票。售票员阿姨和蔼可亲,说小孩子不用买票,不收我的钱。
我在两路口下车后,又转乘3路电车到扬家坪,回家后傻笑着对大人们说哥哥“不见了”。父母大为惊奇,还不相信我自己乘车回来的。
我的“失踪”把带我出门的陈哥吓得不轻,担心我走不回去他担待不起。他满头大汗在城里一直找到下午,只得抱着负荆请罪的无奈,胆战心惊地牵着另一个小学生跑回来,在大人们面前手足无措,哇哇直哭。大人们也是心有余悸,对初中生陈哥一顿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