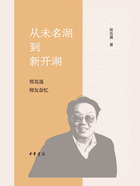
郑天挺先生与史语所
——兼谈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
先父郑天挺先生,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899年生于北京。郑先生自幼丧失父母,未传家学,他的旧学知识,系在学校及自修而成。
郑先生1920年(民国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在校期间及以后共事多年的好友有:郑奠(石君,1895—1968)、罗庸(膺中,1900—1950)、罗常培(莘田,1899—1958,长一班)、张煦(怡荪,1893—1983)等人。毕业后又与罗庸、张煦一起就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从师于钱玄同先生,并在北大预科教书。
20世纪30年代后,郑先生在北大国文系任教,讲授古地理及校勘学等课程,同系中有罗庸、郑奠、罗常培诸先生,时称“二罗”、“二郑”。罗常培先生系史语所老人,1934年刘复(半农)先生去世,才把他请回来。他与郑先生同年同月同日生,关系甚笃,共事亦长,彼此无话不说。
抗战爆发后,郑先生转入北大史学系,1946年至1952年并兼任系主任。1952年后,至南开大学任教,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
郑先生行政事务繁忙,1933年至1950年任北大秘书长十八年;在西南联大时又兼任总务长六年,备极辛劳。
一、郑先生的治学方法与史语所的学风相近
郑先生出身北大,在学校读书任教三十余年。北大与史语所关系本来就密切,而其治学方法与学风亦大多相似。
郑先生治学谨严,精于考证,完全继承了乾嘉以来朴学实事求是的治学传统。他晚年时曾说:“在大学时还是受黄侃、刘师培老师的影响深。”他研究学问扎扎实实,一般不愿写文章;有时已成之稿,亦藏之箧笥,不愿示人。他的佳作《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就是如此,是被罗常培先生再三督促下,才拿出发表的。而文稿一经写出,文字简洁,论断独到,每多为同行所称道。下面谨举他早期几篇论文为例,以见一斑。
《臆测》一文是郑先生的早年著作。20世纪30年代初,北大史学系孟森先生著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一书,其中“太后下嫁”亦为疑案之一。主张“下嫁”论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孟老不同意此说,谓多尔衮皇父之称,犹之汉人之呼尚父、仲父,不能作为“太后下嫁”之证明。此论一出,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郑先生也不同意“太后下嫁”说,他继孟先生之后,作《臆测》一文,依据大量史料,兼及史语所、故宫及北大明清档案,说明“皇父摄政王”是当时的一种爵秩,是为酬报有大功勋之亲王的,即“摄政示尊于国,皇父示尊于家”,多尔衮即因此由亲王、“叔父摄政王”,进而尊为“皇父摄政王”。而这种称谓亦与其左右希旨阿谀,满族之旧俗有关,而“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
这篇文章刊载在当时北大《国学季刊》之首篇,扉页尚配有相关文书及摄政王印等。文章发表后,在清史领域中颇有影响:孟心史先生对文中所述极为赞成;老友张怡荪称赞此文是以最习见的材料,得出最公允的结论。中山大学历史系吴宗慈老教授刚刚写好一篇与孟老意见不同的文章,及见《臆测》一文后,对陈寅恪先生说,“看到‘郑文’后,本想修改一些看法,然已来不及,只好在文章之后附上几笔”,云云。

郑天挺《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
与此同时,郑先生还在另一期《国学季刊》首篇中发表《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一文,这是郑先生用校勘学方法写出的文字。
清中叶以来,一些学人对清代著名学者赵一清颇多误解,认为其著作中有抄袭之嫌。郑先生则认为,看一位学者有没有学问,还应当看看他的其他书写得如何?于是拿“杭书”及“赵书”进行校勘比证,结果证明“赵书”所征引的文献,多于“杭书”七八倍,“捃摭益富,考订綦详”,从而证明赵一清是清代有学问的学者,而不是“攘美窃名之流”的文抄公。
抗战之前,孟森先生曾致函张之洞幕僚许溯伊(同莘)先生,询问张之僚佐“燕斋”为何许人?许复信,认为“燕斋”大约是广东盐使“瑞璋”。收到回信时,孟老先生已归道山,信转到郑先生手中。郑先生依据《张文襄书翰墨宝》中之信札,发现信中之“燕斋”与“蒋大人”为同一人。于是写出《〈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一文,举出五证,证明“燕斋”应即当时署两广盐运使之蒋泽春。郑先生这一结论,只能告慰于孟先生九泉之下了!但这篇考证文字,郑先生比较满意。他在晚年曾说:“这就是在没有什么线索的情况下,如何找到线索、如何进行比证,从而得出较满意的结论。这是最起码的考证方法,年轻人不能不知道。”
抗战后郑先生至蒙自,曾讲授隋唐史,并注意西南边疆史地问题,先后写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一组文章;其中“发羌”一文影响更大。
《新唐书·吐蕃传》中提到吐蕃是“发羌”的后裔。郑先生在读该传中,发现“发羌”很可能即是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于是用唐代有关史籍,以地理证“发羌”之地望,以古音证“发”字与Bod可相对,从而得出“发羌”即Bod对音之结论。此文原名《发羌释》,经罗常培先生改定为今名,并就稿中有关音韵学方面提供了证明。陈寅恪先生对此文观点亦表示同意,并为之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邵循正先生又据波斯文为之补充译文。此文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中。
二、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史语所形同一家
北大在“七七”抗战不久先迁长沙,与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三校又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但三校仍有各自独立的科研机构。
1938年秋,时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的郑天挺先生正因事在上海。他曾写信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建议多点,以求北大之复兴。他认为欲求北大之复兴,必须注意四方面之问题:一曰加强干部;二曰吸引人才;三曰提倡研究风气;四曰派遣学生留学。其中第一点,因文学院院长胡适远去美国,并任驻美大使,估计短期难以回国,因此向蒋校长建议,最好以傅斯年或杨振声先生(曾任山东大学校长)继任文学院长,以加强实力。
此建议蒙蒋校长同意,于是询求傅先生的意见。傅先生表示不愿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乃请杨振声先生继任。
这时的史语所,在傅斯年先生带领下,也与北大一起由长沙迁至昆明。史语所人员不多,但书籍不少,且多善本,这给北大师生以极大的帮助。20世纪30年代中史语所的人员,大多系北大出身,又有傅先生的关系,因此,与北大形同一家,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史语所更是如此。
傅先生原是北大国文系1919年(民国八年)毕业生,与罗常培先生同班,高郑先生一班。20世纪30年代,史语所一度在北平,傅先生亦在北大史学系教课,并不断物色高材生充实史语所。
1939年5月,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先生主持,担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大多由文学院院长兼。当时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虽任驻美大使,但文学院院长的名义尚保留,傅先生实际亦是代胡先生主持工作。傅先生事情太多,对研究所难以全面兼顾,于是他就拉郑先生任副主任,协助工作。是年夏天,北大文科研究所正式招生,先后招过两次。
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有傅斯年、陈寅恪、汤用彤、杨振声、唐兰、姚从吾、罗庸、罗常培、向达、郑天挺等先生;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先生,亦系所外导师。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使北大与史语所俨然一家。

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时与学者恳谈交流,右起:郑天挺、吴晗、毛子水、俞大 ,左一傅斯年
,左一傅斯年
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城内青云街靛花巷三号租用一座三层共十八间房的小楼,这座房子本是史语所租的。北大几位导师如陈、汤、姚、罗常培及郑、向诸人都住在楼内,傅先生如来城内,也住于此,每人一间。当时研究生亦住在楼内,食堂、图书室皆在其中,切磋问题极为方便。每当茶余饭后,都是闲谈及探讨问题的最好机会,尽管条件比较艰苦,大家钻研学问的热诚始终高涨。当时傅先生与郑先生即要合纂新的《明书》,两人详列目次,期以五年完成。只因战事紧迫,史语所又迁四川,计划乃搁浅。
昆明城中敌机轰炸频繁,史语所还在昆明北郊龙头村宝台山响应寺租了一些房子,所中的同仁即在此处工作,所内图书亦存放于此,阅读非常方便。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读书作业,从未间歇。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亦同样在此从事撰述,可谓美不胜收。
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务活动
傅先生对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非常严格。每逢口试,他多参加主持。众导师亦就某一问题向考生反复询问,直至考生语塞为止。然尽管所问严格,其目的并非要求全答,而是在测验考生之知识面,亦非单纯之下马威,故意刁难。
研究所经常请一些所中导师及专家来所报告,如汤用彤、闻一多、刘文典等教授均在邀请之列。1941年,夏鼐先生由英归国,到了昆明,亦曾被邀演讲。同年夏天,老舍先生亦来所中作报告,并在研究所住了几天。英国学者李约瑟、休士到昆明,均曾在所下榻。
1942年后,所中还派向达先生去敦煌参加西北考察团事宜,这是北大与中央研究院的合作项目,是郑先生特别关心的一桩事。1942年2月6日,郑先生即给傅先生一信,询问向先生行期。信中道:“西北考察事如何?向公等何时成行?甚念。”(1)郑先生的日记中亦谈过此事。1943年1月17日,“锡予(汤用彤先生)来,示以觉明(向达先生)敦煌来书,随与之长谈(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余意,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若历史考证,此后惟敦煌一路。其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关涉甚多,影响甚大。此后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吾辈正宜追踪迈进”。(2)又,1943年10月11日,郑先生亦致向先生信,劝其仍赴西北考察,并表示“所得古物,北大不争取,但保留研究权;如有需要参考时,其它机关应充分供给”云云。(3)
此外,即文科研究所诸生留校工作事,郑先生对当时陈寅恪先生之隋唐史研究生汪篯爱护备至,希汪能留在北大任教。
汪篯当时是陈寅老的学生,郑先生也以导师名义协助指导。陈老1940年6月离开昆明后,汪又由郑先生继续指导。1942年2月6日,郑先生曾为汪留校事致函傅先生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柢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作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4)
1947年,汪先生果来北大史学任教。直至1966年,“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四、史语所迁川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当时在昆明的北大及史语所同仁感到非常震惊。那天晚上,一些人正在蒋梦麟校长家中闲谈,钱端升先生忽然来了,说:“刚刚听到香港广播,蔡先生去世了。”
蔡先生去世后,研究院及史语所的同仁总不免有些各自的想法,有时还或多或少有些悲观。在一次闲谈中,傅先生及李济先生均流露出“树倒猢狲散”之情绪。当时郑先生也在座。他闻后颇多感慨地说:“孟真、济之皆目前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尚且如此,真是国家学术机构之不幸。”
由谁继任院长,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许多人选自然都在大家考虑之中。其中有人主张由北大蒋梦麟校长继任的。陶孟和先生就私下对郑先生说:“看来这次梦麟先生应当出来了。”
1940年秋冬,日本侵华战争日紧,处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及史语所等面临着新的搬迁。政府原让西南联大再迁,遭到学校教授的反对;只在四川叙永设立了分校,让这年刚入学的新生前去上课。史语所则决定迁往四川李庄,傅先生也于1941年1月飞川,筹划一切。从此他一直未来昆明,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重回昆明,这时他已是北大代理校长了。
史语所迁川后,由于当时局势紧张,北大又缺少书籍,郑先生很为文科所诸生的培养前景担忧。他曾一度主张北大文科所可暂时依于史语所,以使诸生得以更好培养。他在1940年9月7日,曾在致傅先生信中谈及此事:“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今后所址,非追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甚以为然。但细思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轫始,岂不大糟!弟亦知若此十余人追随史语所离开联大,在史语所,在吾兄均增加无穷麻烦,但此外实无他策。弟意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一地,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兄意如何?如兄意以为可行,则此时即可准备起来也。”(5)
此事当然涉及问题甚多,史语所的负担也太重,但后来傅先生还是允许四位先生去了李庄。
史语所迁川后,在昆明靛花巷及龙头村的房子就移作北大文科研究所利用了。汤、罗、郑几位先生一直住在靛花巷,直至抗战胜利(罗于1944年11月离昆明赴美)。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先生亦随史语所同往四川。1941年6月,郑先生与罗先生还特意到李庄史语所去看望他们及他们的导师,为这四位的论文答辩做些准备工作。罗先生所著《蜀道难》一书,对他们这次访问史语所,也有较详细的叙述。
由于史语所迁川过于仓促,与云南省政府关系弄得有些僵,以后诸如民族、语言调查等事项,交涉时还以北京大学出面。1941年8月7日,那廉君先生致马学良先生信说:“关于向云南省政府索取护照一事,当由弟呈告傅所长。傅所长之意,以为本所去年迁川时,与云南省政府(关系)弄得非常之坏,如由本所或本院出名向其索要护照,必遭碰壁。故不如请兄商请郑毅生先生,借用北京大学名义,由北大函咨云南省府发给护照,并请其转饬禄劝县政府予以保护及协助,不但成功性较大,且以在滇之机关请求之,自易办到。此事请径函郑先生,恳郑先生饬人一办。或托任又之(继愈)兄特请郑先生,均无不可也。”三四十年代的北大与史语所,确实是彼此不分的。

1961年郑天挺与陈垣(右)合影
本文承蒙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提供信件复印件,特此致谢。
(《郑天挺先生与史语所》原载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10月版;《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兼忆傅斯年、郑天挺先生》原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版。本文系此两文合并)
(1)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存档III1069。
(2)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659页。
(3)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752页。
(4)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存档III1069。
(5)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存档I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