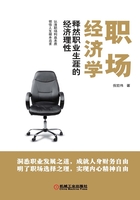
一、系统认知社会价值与道德重构
大到全社会,中到各类组织与企业,小到我们每个人,文化及其价值信仰的建构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那么,面对我国社会文化的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办呢?这就有必要对社会价值与道德重塑进行系统认知与交叉审视,以寻求可行的对策。
(一)社会价值与道德重塑的认知脉络
1. 关于我国社会当代价值重塑的重要观点
张建宁(2008)认为,当代中国信仰重塑有三大重点:(1)要走向科学的信仰体系。信仰的科学化包括对科学的信仰和科学地对待信仰两个方面,人类最好、最有效的信仰来自科学。(2)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一个民族由于它所特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质,总是存在着共同的精神凝聚力和共同的理想信仰。当代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和信仰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富强。(3)把加强道德信仰建设作为当代中国信仰重塑的基础。作为代表着人类最基本的真、善、美的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道德信仰通过个人内在的心理接受而发挥作用,靠自觉遵守而不是强制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顾远(2001)认为,建构我国现代化新文化,即理性主义文化的内涵是:建立一种能够推动现代化的新文化,它既不应沿袭实用理性的传统智慧,也不该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理性。这种新文化应该包含了中西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具时代性。抛开实用理性的消极方面,剔除理论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追求真理。
王石泉(2011)认为,我国要建设新的文化应当讲究“综合与中庸”,即以中国传统智慧加上西方好的文化思想,再加上“与时俱进”观念,就等于“应当的中国文化”。就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而言,正如蔡晓辉(2014)所指出:无论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还是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于当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成长中的烦恼”而言,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蕴含着重要的启示。
2. 社会价值与道德重塑的分层建构与渐进跃升
怎样走出“以满足感官享受为人生内容、以跟着感觉走为人生哲学的感官主义的当下文化”的社会文化价值迷惘?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主要价值观的最新理论观点进行整理,可知这对于我们的管理启示是:社会道德大厦是有层级区分的,社会价值重构应当有一个分层建构与渐进跃升的过程,社会价值重构的关键在于把国民价值信仰的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与下述的国外公民文化道德教育理念分析的管理启示是相互吻合的。
中央党校教授阮青(20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动力论”的观点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价值观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国家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价值观;我们也不能把对社会先进分子的要求,简单地等同于对全体人民的要求。比如,学习雷锋的问题,人人可以成为雷锋仅是一种理想,有人不能成为雷锋则是现实。由此可见:国民文化道德教育应当区分层次,区别对待。对社会先进分子适用于较高的文化道德标准,而对普通人民的文化道德要求当有层级的区别。其社会文化管理的本质正如张建宁所言:“道德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由此看来,社会的道德大厦是有结构的,不同层次的人应当有不同的做人道德底线。吕会霖曾将社会道德大厦结构分为五个层级: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半公半私,先私后公,自私自利。由此可见,社会道德的提升也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上台阶。
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王石泉(2011)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政治文化是不够的。一个国家没有政治文化是不行的。”其第一句话的逻辑含义就是,政治文化适用于精英阶层人士。换言之,“政治价值不是放之四海的普适价值,政治价值具有鲜明的党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治信仰只能作用于政治家、政党骨干或少数有特殊政治兴趣的人,对多数民众是起不了作用的”。
(二)国外公民道德教育理念的观察借鉴
这里就新加坡、德国的公民文化道德教育理念加以简要分析,以期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提供借鉴。
1. 新加坡全民文化道德培育的经验与成效[1]
新加坡是东方传统文化下的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国家,1965年独立以来的50多年中,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崛起为令人钦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强国,对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圈可点的经验确实很多。新加坡被誉为“世界上最有规矩的城市之一”和“东亚现代文明典范”,2015年9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显示,新加坡是亚太地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全球反贪机构国际透明度组织发布的2015年廉洁度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八,是排在前十名的唯一亚洲经济体。新加坡既取得了经济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又取得了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令人羡慕的成果。这源于新加坡举国坚持不懈地推行公民道德教育,构筑全民价值体系。由此,确立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巩固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增强了国家凝聚力,为新加坡的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新加坡“文化朝东看”与“五观”“八德”的核心价值。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提倡“在技术上学习西方,在精神上倡扬东方”,注重以中华文化的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来武装全体新加坡人的头脑,以自觉抵御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这就是新加坡的“两看”:文化朝东看,经济向西看。早在1978年前后,新加坡即通过“文化再生运动”,反对全盘西化,倡导东方价值观,核心就是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儒家文化基础上培育现代的东方价值观,对传统的“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赋予了现代意义,并将其作为新加坡的“治国之纲”和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
新加坡被称为“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千国语、容纳万种宗教”的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国民中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他们信仰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在这种复杂的种族与宗教背景下,为了促进多元文化社会的团结与稳定,1991年,新加坡以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方式,将五项共同价值观(简称“五观”)作为新加坡国民共同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
纵观新加坡“文化朝东看”的公民道德教育,以“五观”“八德”为核心实行高度聚焦,并贯穿于始终,形成文化培育的合力,其中有两大重点和一大机制:
第一,重“国家意识”确立。在人种、信仰、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为避免种族矛盾与宗派纷争,统一国民思想,大力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明确提出,必须使各种族移民及其后裔加强对新加坡的认同。新加坡政府注重培植公民的国家意识,以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国民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责任感,并在这一旗帜下为新加坡而奋斗,增强公民的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重“公民意识”教育。注重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培养。新加坡政府将公民意识教育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新加坡政府十分强调尊重国情,尊重人民的选择,拒绝照搬西方民主,拒绝任何将西方民主强加于人的企图。在整个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坚持求同存异、和谐宽容、团结协作的方针,极力倡导以东方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观。“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是新加坡公共的善,也是新加坡公民可以充分分享的最崇高的道德权利,为此新加坡公民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履行道德义务,在必要之时“贡献自己的生命”,由此还建构了“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实效”的新加坡精神。
第三,道德教育的法制化保障机制。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把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也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严肃法纪,严格治理,注重“他律”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公民道德建设他律的实现途径在于制度规范的确立。道德效能的发挥仰仗制度的保障,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离不开严格的法律制度的保障。教育和惩罚一直是新加坡治理国家的两手。新加坡的奖惩具有自己的特点:奖惩的标准与提倡的道德准则具有一致性而不是相反;令行禁止,贯彻始终。“违法必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一种普遍要求,但大都流于形式,重罚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但新加坡则是真正地做到了“违法必究”,树立了法律的威严,切实发挥了他律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新加坡不断从失败和曲折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而又运行良好的公共法则和制度。
(2)新加坡政府主导促进全民对“五观”“八德”的共识与践行。在新加坡政府的主导下,以固定文化周和各种活动为主要载体(类似于工具价值观思维的方式与方法)的公民道德教育,促进全民对“五观”“八德”的共识与践行。新加坡政府每年倡导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多达30种,如:忠诚与国家周,对此每年举行两次全民大讨论,并形成国家白皮书;敬老周,也就是弘扬“八德”之“孝、仁、爱”(即终极价值观)的工具价值观活动与形式;睦邻周,用以和谐复杂的种族与宗教背景下的人际关系,以此促进“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的国民共同价值观念的共识与践行;三大人种周,以此协调印度人、马来人、华人三大种族关系,促进“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国民共同价值观念的共识与践行。此外,还有劳动力周、礼貌月、华族文化月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以活动为载体推进全民文化共识。新加坡每年还要搞七、八个运动,比如:生产力运动,类似于我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活动;文明礼貌运动;防止犯罪运动;反对乱扔乱吐运动。在新加坡国民道德教育的各种活动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爱神运动”,即“以教堂活动管思想”。新加坡对国民思想教育是在教堂进行的。我国军队有“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而新加坡国民思想教育则是比照欧洲的“教堂建在村上”的理念来进行的,还流行一种“八管”的说法,即“教堂管思想,警察管行为,政党管平衡,政府管协调,社会管保障,舆论管监督,法院管对错,个人管挣钱”。于是,新加坡政府在“政府管协调”中,搞了一个“共同祈祷书”,每当人们在新加坡教堂里做祈祷时,先要一同朗诵“共同祈祷书”的内容,然后再念自己所信奉的教派教义的内容。新加坡以“爱神运动”来配套管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新加坡“五观”“八德”国民共同价值观念体系的落地进程。
经过不懈努力,新加坡政府在2010年年底的国民教育调查结论是:无论是小学、中学、初级学院或高级中学,学生都对国家的未来有信心,也有很强烈的归属感,95%以上的学生对身为新加坡人感到骄傲。学生公开表明他们爱新加坡,喜欢新加坡的任人唯贤、种族与宗教和谐以及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等特质,10个受访者中就有9个相信他们能让新加坡更美好。由此可见,新加坡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是:政府重视公民道德教育;“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公民道德教育“润物细无声”;家庭、社会和学校齐抓共管。因而也使新加坡被誉为“世界上最有规矩的城市之一”和“东亚现代文明典范”。
2. 德国的“朴素道德”理论和“善良教育”
20世纪60年代之前德国也曾搞过崇高伟大的道德教育,但效果不理想,社会环境也不好,出现了颓废与垮掉的一代。然而,他们并没有责备青年人,而是从道德思想教育的内容上找原因,发现崇高伟大的道德教育与年轻人认知有很大距离,使其难以接受。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道德教育的重点转移”,即从崇高道德教育转向朴素道德教育,取得较好的效果。吕会霖(2002)认为:朴素道德最符合人性,它讲的是做人的起码道理,是人们最能接受和比较容易做到的;而高层次道德接受的前提是人要有一定层次,道德的提升要一步一步地上台阶。
“朴素道德”理论由当代德国教育家鲍勒诺夫提出。他认为:人类社会中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更普通、更纯情、更基本、更长久保持同一性的道德,如诚实、信赖、同情心、爱、关心等,它们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朴素道德具有自然健全性,是基于人类本性和社会生活的,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流露。
德国国民朴素道德教育五大规范:第一,要自觉忠实地完成每个人在特定活动范围内的责任;第二,要老实坦诚地和人交往,踏实、正直,做事不半途而废;第三,同情他人和理解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痛苦,乐于帮助处于困境的人;第四,尊重他人活动的权利,与人为善;第五,言行举止端庄,注意倾听别人意见,做受人敬重的人[2]。
国外公民文化道德教育理念分析的管理启示在于:第一,社会道德大厦有层级结构之分,国民的道德提升与文化培育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上台阶。第二,国民道德建设与社会价值信仰重构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鼓励先进,照顾多数,不能把对社会先进分子的要求,简单地等同于对全体人民的要求,组织文化只有被普通员工所信仰才具有真正的管理学意义。第三,要高度重视达成国民文化道德共识与践行的具有工具价值观思维的载体与活动。文化共识的培育过程是一种集各种管理理论及其方法于一体,将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相融合的综合管理过程。